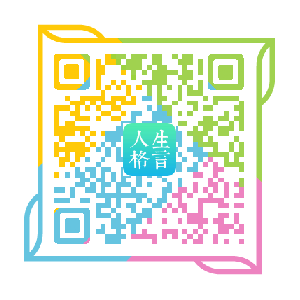《危机与重构》是一本由李碧妍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80元,页数:5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一):不太适合一般读者的好读物
这本书依旧是几位朋友在一起共同阅读的书籍,被标题吸引——正如书中陈文:一般历史教材中,唐朝进入安史之乱后面篇幅极为短少,而在历史教材内容安排上,“盛唐”时代的内容又相对极为厚重,极容易让学生从直觉上认为唐朝进入安史之乱之后就立即帝国崩塌,历史事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而读完这本书第一个感觉也是愈发觉得历史的复杂,历史学的艰深。
如同标题一样,并不是否定本书的价值,而仅仅是给一些非历史学背景读者,一些业余爱好者,以及一些和我一样的“社会人”提供一些读前启示:
1、这是一篇博士论文。需要一定保持清醒,个人当年是一名理科博士,自己也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但是理科和文科之间写作还是有一些区别,另外更多的是源于文理科的天然区别,理科的证据更多是一些纯数据,或者转化的图表,甚至学界一般对图表有“自证”要求,即图表单独拿出来,读者能够不借助正文文字辅助完全能够理解图表所传达重要信息。不过文科里大量的证据都来自一些古籍(《资治通鉴》、《旧唐书》、各种墓志铭等等),所以对古文功底要求就不用更多了。
2、这是一本需要完全沉浸阅读的图书。由1可以知道,这肯定不是一本《明朝那些事》,春节在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看到一位博物馆馆长在评价《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综艺节目虽然基于一些历史事实,但是为了效果,总是会偏离历史事实 ,所以在不多几次看节目过程中,我经常留意到里面顾问团们说到:”基于历史,作了合理的推测”。回到这本书,因为是一本学术专着,准确是第一要位,里面的逻辑链条,证据举证都是极为严密的,因此很难用一些娱乐的文字去辅助描述。就如同一般博士论文里,是不允许用一些形容词的。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会有些累,最初我买了实体书,试着在地铁上看,实在是无法确实的融入进去,最终选择在假期完全抛开一切啃了过去。
3、这是一本价值很高的书籍。学术专着的本质属性就是从作者角度出发,去解释一些过往的偏见,发掘一些过去未曾看到的东西,历史学又如此经常受主观记录人的影响,甚至不同时代社会观念影响,都可能会对同一件事实,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未来,对唐朝的历史问题,观点依旧会有些变化,但是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目前极好的研究基础。
4、一定要采取一定的战略性阅读。虽然这本书价值很高,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位历史学研究者,刚开始读的时候,还是逐字逐句的阅读,发现实在是吃不消。这本书里面大量的举证段乱,从我阅读过程中,就作了战略性的放弃。书中经常会采取这样的逻辑方法,对某一个问题做了一个回答,后面会针对这个回答中的,人物、时间、过程举出大量的正反例子,更多时候会引用原文,我在后期阅读中,一是为了节省时间,二是秉着科学的默认信任研究者的精神,我就直接看作者的推理过程。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阅读建议,当然对于一些在校学生来说,我极度建议完全读完,因为是一次很好的思维训练。然后对于一个只是想获得一些谈资的读者,我建议直接读各章小结和最后结语。
.S. 千万不要读电子书,这本书需要经常前后翻页,电子书极为不方便。
中央与地方,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古至今,中国、美国各个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如何实现,一直都是政治家们所探讨的事情。而一旦中央和地方之间失衡,如何重新构建新的平衡,却极度体现统治者的智慧。
显然,我们从唐朝末期的统治者的行动来说,也可以看到随着统治阶层能力下降,地方力量势必会反弹——这可能是宋朝学习的一个方面。但是宋朝为了避免地方反噬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阉割自己,可以看到从宋朝开始,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逐渐消失。
安史之乱对唐朝最大的打击在于,中央政府的统治者们开始很难相信别人,既不敢放权给地方,甚至对于帝王子孙,权利的让渡都夹着极大的猜忌和防备。我们都无法从史实中发现,这种猜忌和防备是否是促成功臣反目,父子成仇的原因,还是这只是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个年代,信息沟通不畅,很多信息从研究者出发极为浅显的道理,可能在当时很难形成统一的参谋意见,很多时候帝王还是依靠着近臣。从管理角度出发,信息的分散和隐藏,可能就是导致很多简单的事情无法迅速实现的最大的障碍。人类是否能够实现三体文明那种不撒谎的完全信息沟通,似乎应该是避免人类文明不停的在诞生-发展-顶峰-衰亡的历史演化中重复的一个条件。
另外,从历史角度来说,我还是要重申一下,个人的历史观:在历史潮流中,个体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一个上帝扔色子的过程。个人努力能够改变概率,但是不改变最终结局——有些历史决定论的感觉了。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二):藩镇时代的启幕: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藩镇时代的启幕: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史研究历来偏重唐前期,对于中后期关注不够,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多有改观。就专着而言,先有谭凯(Nicolas Tackett)关于世族衰亡的专着,后有陆扬对于晚唐清流文化的阐发。[1]前者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晚唐的消亡问题,认为黄巢(?-884)之起,特别是对长安的占领和屠杀从肉体上摧毁了这一阶层。后者主要从对唐代中后期世族中潜行的清流文化的揭示,看其政治文化在唐后期五代的赓续问题。总体而言,这两本书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强调黄巢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世族消亡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强调世族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成为唐中后期的时间界限,主要在于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基于此,学界对两次事件本身的相关研究,历来十分丰富。[2]此外所涉及到的问题,则是普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及其割据现象。这是讨论唐朝中后期的历史所绕不开的问题,近年来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3]而在人们接受了唐代中后期藩镇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整个藩镇时代的兴衰,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对此,50多年前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作为对藩镇衰落之势的代表性研究,至今无人超越。[4]而本文所评新近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以下简称“李书”),则可作为研究藩镇启幕目前最全面的成果。
一
《危机与重构》是一部政治、军事史著作,是作者李碧妍在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李书除了绪论、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和附录(《李怀让之死》)外,共分四章内容。关于李书大致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心路,作者已经在一次公开对谈中予以详述。[5]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作介绍: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先就该书整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和步骤予以概述,然后梳理和反省中外学界藩镇研究的成果。就成果而言,作者根据两种基本思路整理,即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前者多为中国学者所关注,后者多为日本学者所关注。(第5-14页)作者本人的计划,则要打通和兼顾这两方面。当然,一般著述绪论多先介绍学术史,再概述全书结构。所以,作者若能换个顺序,在学术史基础上,就该书所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介绍,应该会更引人入胜。
其次,作者分四章,分别讨论了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大区域之中,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产生的种种动向。特别是各藩镇最初创设和撤销,藩镇辖区分割与合并,藩镇军力来源多样化,以及藩镇节帅和将领乃至基层军士的各种心态变化。
第一章《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正所谓“渔阳颦鼓动地来”[6],安史之乱爆发于幽州一地,逐渐波及整个北方。但作者显然并不是专门研究安史之乱,故而将目光首先聚焦于安史之乱战场所在地,特别是名闻遐迩的睢阳保卫战之发生地——河南道。并由睢阳之战的惨烈情况,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唐廷与地方军事力量之间的纵横捭阖之势。当然,睢阳之战也只是一个开篇,本章重要内容包含三点:一是通过梳理唐廷先后任命的李光弼(708-764)、王缙(700-781)和裴冕(703-770)三任“河南副元帅”(第43-55页),以及历任河南节度使(第32页),揭示了因安禄山叛乱的前车之鉴,导致功高震主的平叛将领在此后的不再受信任,以及在逃亡蜀地的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和称帝灵武的唐肃宗(711-762,756-762在位)之间的人事矛盾;二是通过梳理河南节度、永平军这两个最终一步步被切割的藩镇之兴衰,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已经形成割据之势的河朔和淮西藩镇,对河南道藩镇格局的逐渐定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第57-74页);三是对平卢系藩镇的再次探讨,特别是平卢军被一分为三,是元和(806-820)中兴的一件大事,故而得到历代学者的充分关注,但作者这里更想要强调的是在早期藩镇分合基础上逐渐出现的新型藩镇,经过平卢系将领的不断消亡,而慢慢走上“骄兵”主导政治的道路。(第104-111页)
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此章着重梳理了安史之乱及其后京西北八镇的形成过程,长安、洛阳两京之间三个据点(河阳、陕、潼关)的兴起,和神策军的兴起及对关中兵力的填充。就朔方军而言,作者认为,前辈学者对朔方军的研究,或“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第115页),或即便整体考察京西北八镇,“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第116页)。亦即,作者认为早期朔方军和后期的京西北八镇,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动态过程”(第117页)未能被学者予以揭示。虽然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各位学者文章所要讨论的重心分不开,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所研究的内容之不同。但作者所选取的这一视角,确实能够从她的角度来揭示这样一种因党项、吐蕃的入侵而设置京西北八镇的动态过程。就长安、洛阳之间三个据点而言,这三个据点在安史之乱期间显示出的重要战略位置,日后逐渐发展为三个河阳、陕虢、同华三个藩镇,成为唐廷与河北割据藩镇之间沟通的一个中间地带。具体而言,河阳为守卫洛阳的前线,陕虢有“藩垣二京”(第205页)的作用,同华则不久即分为两个只领一州的“非完全节镇”(第207页),以保证关中东大门的畅通。就神策军而言,因为涉及到中晚唐禁军的形塑,乃至五代、北宋时期禁军的膨胀,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神策军在关中驻军点的分布,及其反映的唐廷对于防止吐蕃侵犯的考虑。特别是对于神策军驻地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三条平行线的揭示,颇为直观。(第211页)
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河北是燕政权安禄山(703-757,756-757在位)、史思明(703-761,759-761在位)的大本营,以及日后典型割据藩镇的所在地,故而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安史之乱时期和乱后初期的河北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由于河北道范围广大,民族成份复杂,每个州境所体现的功能皆有不同。所以作者多次划分河北地区。或以幽州为坐标,分为燕南、燕和燕北三部分,其中燕指幽州和从幽州分出来的蓟州,燕北至妫州、檀州、营州、平州、安东都护府,幽州以南的其他地方总称为燕南。(第261页)或以是否“边州”为标准,将燕、燕北诸州归为边州地区,恒州、定州、易州、莫州、瀛州、沧州归入次边州地区,再往南则为河北南部地区。(第267页)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划分,为作者进一步对安史之乱期间河北地区军政动向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即经过作者的梳理,安禄山军团的主要来源于边州地区的蕃人(第271-274页),而普遍设置团结兵的燕南诸州相对而言不受安禄山军团所控制(第274-278页),故而造成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地区朝叛之间激烈的冲突。之后,作者更进一步梳理了后安禄山时代的河北军政动向,特别是揭示史思明利用礼仪手段努力整合已经散布于河北各地,且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路叛军。(第286-288页)不过这种努力并未能够在史朝义(?-763,761-763在位)时期得到持续,最终也因史朝义的失败,以及各地不同将领的向背,而使得河北地区在名义上回到唐廷统治之后,分裂为不同的藩镇。在梳理了河北藩镇成立史的基础上,作者方才进一步探讨这些藩镇的后续性格特征之奠定情况。当然,由于对之后河朔藩镇的研究,学界已有许多精湛的分析,故而作者沿袭较多。值得重视的发明则是在渡边孝的基础上,对“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这两类藩镇形态的进一步区分,颇有说服力。(第328-335页)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安史之乱爆发于北方,主要战场也局限于北方,但不可避免会引起北方人士南下避乱,以及唐廷出于经济的需求想要极力确保南方的安定。因此,无论南北,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李书第四章即讨论了南方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历史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历史面相。首先是永王璘(720?-757)事件,作者通过对永王璘南下赴镇途中与地方士人的交往入手,讨论了在唐玄宗尚在蜀地,唐肃宗已然即位于灵武前后,各方人士的政治动向。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对各类诏令颁布时间的质疑,以及所颁布诏令本身之真伪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肃宗通过利用篡改史料来塑造自己合法性。(第393-398页)永王璘事件,实际上可以视作唐廷不欲将与安史旧部之间的妥协手段(设置藩镇)用在江淮地区。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财运\的畅通,避免藩镇跋扈造成影响财政收入。随后,作者先后讨论了刘展(?-761)之乱、韩滉(723-787)“骋志”(第485页)和李锜(741-807)叛乱三次事件。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对三次事件始末的揭示,论述了唐廷不欲在南方地区纵容类似北方节度使体制的意愿,即致力于将“节度使体制”转化为“观察使体制”,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至于此章最后一节对松井秀一所谓“平静期”(第523页)的探讨,其核心在于揭示土豪层的兴起及其对唐末五代南方历史的影响。
以上四章内容之后,作者以《藩镇时代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代结语”,揭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意义。目前学界对于中晚唐五代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不过虽然最早在民国时期,即有于鹤年对“藩镇”意义的提示[7],但至今对藩镇的研究重中晚唐,轻五代十国。
二
综观李书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以熟练的史料、优美的笔调,给大家呈现了一幅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半个多世纪,甚至延伸到唐末五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对于李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动态的过程来展现安史之乱的不同面向,因为这场乱事并不是一部预先安排好的剧本。这一点,书评人维舟已有较好的评论:“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8]笔者对安史之乱并不熟稔,但读完全书之后,基本能够勾勒出唐中期的政治、军事动向。是为此书一大功劳。当然,作为书评,也需要一些“瑕不掩瑜”之“瑕”予以指出,以期继续完善。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开篇提及了《新唐书·忠义传》所载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东巡的事件(第15-16页),又在把张巡(708-757)之事梳理一遍后进一步指出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并未经过当时的应天府(唐代的睢阳),从而展示出《新唐书》编者欧阳修(1007-1072)的一种“杜撰”。(第33-34页)然而,根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本栋博士的意见,作者误将宋真宗“东封”泰山比附为“东巡”亳州。即宋真宗曾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至十一月东封泰山[9],也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东巡亳州并在回程途中经过应天府[10]。如此,李书根据错误的映证所绘制的图2“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东巡路线图”(第34页)也就张冠李戴了,而欧阳修关于宋真宗东巡经过应天府的记载也并非“子虚乌有”(第34页)。[11]明确这一点,作者在欧阳修虚构基础上进行的各种推论,也就不成立了。
其次,需要讨论地名(特别是地域名、藩镇名)的断句问题。在没有现代意义上标点符号的古代,断句并不成其为大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始于古籍点校的需要,以及中华书局等古籍类出版社在出版繁体竖排点校本时,划专名线的需要。而学者目前又严重依赖于点校本,故而点校本的点校,以及专名线的标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理解。在李书中,作者所引史料的标点,可以说基本按照点校本进行。不过,点校本的断句和专名线,并非没有瑕疵,使用时尚需谨慎对待。就李书而言,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地域名的断句。比如作者在第一章讨论四镇之乱时的运\路危机时,引用了《资治通鉴》建中二年(781)六月的一段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12]作者引文则为:“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第81页)可见,作者除了给“甬”字括注可通用的“埇”字,以及未引最后一句外,其余内容皆从《资治通鉴》的标点,只是去掉专名线。亦即,作者并未认识到,或并未在此指出,其实“蜀、汉”、“江、淮”、“闽、越”,都不必用顿号顿开,即应该是“蜀汉”、“江淮”、“闽越”。这里的情况,反映的是对某个大地域范围的简称,即“蜀汉”是以蜀地的蜀州、汉州合称,作为对整个剑南西川镇的指代;“江淮”是指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区,也就是淮南镇;“闽越”则指代福建地区,其称呼当取自秦汉时期的闽越国。其中,笔者之所以将“蜀汉”视为西川的代称,是因为“汉”字也可以指代汉水两岸的山南东道,如作者在论述唐德宗(742-805,779-805在位)让淮西节度使李希烈(?-786)讨伐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781)时,即引《资治通鉴》,谓李希烈“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第79页)根据上引文,提及“蜀汉”等地域,是指这些地方“所在出兵”,而当时梁崇义既然站在唐廷对立面,自然不可能出兵。另外,“江淮”之所以指代淮南镇,也涉及到作者未引的最后一句“江、淮进奉船千余艘”,盖若断开“江”、“淮”,以之为二藩镇名,则并无相应藩镇对应,亦无所谓“江州、淮州进奉”之理。至于“闽、越”断开,亦不辞,盖若以“闽”指代福建地区福、建、泉、漳、汀五州,则时有浙东镇越州,不知“越”将指越州及其所属浙东镇,抑或整个先秦越国地域范围,乃至百越地区?因此,作者此处袭用《资治通鉴》断句而未能加以辨析,是稍感遗憾之处。
此外,对于地域名的断句,除了与理解原文表面意思有关,也涉及到唐人的地域观念。比如再来看上面这条引文,其中将“关中”纳入“内”的范围,将“蜀汉”纳入“西”的范围,将“江淮、闽越”纳入“南”的范围,将“太原”纳入“北”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自身统治地域广度的认识。即以关中为核心,所谓“内”;以外的地方,则从对三个方向上的相关地域来确定整个王朝统治地域的范围。从这一范围来看,唐德宗时期的唐王朝,其所能控制的地域基本也是如此。第一点,是当时已经失去河西走廊地带[13],故而“西”的方向从西域转移到西川;第二点,其中未能加入“东”这个方向,乃是当时正处于四镇之乱,最能代表“东”这个方向的平卢镇正在对抗朝廷;第三点,“北”的方向以“太原”,即河东镇为代表,反映出河朔三镇其时也早已自立;至于“南”的方向,范围更加广泛,原本地理上最南端应该是安南都护府,但安南都护府本身并无多少军力,此时也不可能出兵援助,故而以当时大概确有出兵的“闽越”,即福建观察使所辖作为最南的代表。[14]总的来说,可以从这里的方位与地域的对应,看出唐德宗时期,唐人对于王朝统治地域的认识随着政局和领土的变动而改变,这也影响到唐人对于东南西北方位认识的调整,以及对于内外之别的认定。当然,更可以结合作者在书中关于“关中本位政策”和“中央本位政策”的探讨(第536-543页),进一步发掘其意义。
二是藩镇名(以及节度使)的断句。由于藩镇时代的藩镇名,早期多以地名(道名、州郡名)命名,比如范阳、河东等等。故而当藩镇日渐散布于内地之时,也多以地名,特别是所辖地域最主要的两个州(其中前一个一般为节度使治所州)的名字之连称,作为对这一藩镇的一种通俗性称呼,比如泽潞、魏博、淄青、陕虢等等;或者以节度使治州(府)作为对这一藩镇的称呼,比如镇州、河中等等。同样,节度使名,也是如此。比如早期的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后来的泽潞节度使、魏博节度使、同州防御使、河中节度使等等。这样的书写,大多数是在纪传体史书如《旧唐书》、《新唐书》的列传,或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等行文之中出现。在官方文书的行文中,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称呼则有差异。以出镇制文为例,《唐大诏令集》有上元二年(761)六月《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其中记李鼎原有职衔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凤翔尹兼御史大夫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保定郡开国公”[15]。这条职衔中,“行凤翔尹”、“充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是李鼎真正就任的实职。可以看到,李鼎当时首先是凤翔府的府尹,其次是凤翔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的节度使、观察使。再来看作者在书中对李鼎职衔的记载,她从凤翔镇辖境扩大的角度写到上元元年(760)首任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的职名又称‘秦陇节度使’”,以及当年底第二任“李鼎的职名又称‘兴凤陇等州节度使’”。(第138页)作者所引之“秦陇节度使”、“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出自《旧唐书·肃宗纪》,原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分别为“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16],“以右羽林军大将军李鼎为凤翔尹、兴凤陇等州节度使”[17]。可见,作者基本遵从了点校本的断句,将“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分别与“凤翔尹”区分开来,并根据点校本所用的顿号,视之为并列关系。然而,从前引《李鼎陇右节度使制》可知,李鼎所任之“凤翔尹”外,实为“本府及秦陇兴凤成等州节度观察使”。亦即,凤翔府本身也在节度、观察之列,而非将凤翔尹与所谓“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并列。当然,作者原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并不在此,也并不一定有将“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视之为单独的节度使名称的看法。但是,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而来的这种断句,显然影响到了作者对史料的使用,而作者将所谓“秦陇节度使”和“兴凤陇等州节度使”单独列出来,也会影响读者的判断。事实上,《旧唐书·肃宗纪》的这两条记载,应该再加上“本府”二字。这一点,《旧唐书·肃宗纪》上元元年八月己卯条的记载就比较准确,其载“以将作监王昂为河中尹、本府晋绛等州节度使”。[18]河中尹所治仅河中府,故另加“本府晋绛等州节度使”,即河中府、晋州、绛州等州的节度使。
上段详论凤翔节度使名,主要是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作者对点校本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读者的观感,导致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误解。比如作者在讨论建中三年(782)七月李希烈兼任平卢节度使讨伐李纳(?-792)时,引用点校本《资治通鉴》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第83页)其之所以在“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之间加顿号,是依从了点校本《资治通鉴》原文对“平卢”、“淄青”、“兖郓”、“登莱”、“齐州”这五组词分别划专名线[19],即点校者大概认为这五组词分别代表五个藩镇或五个节度使。事实上,这里首先不必在《资治通鉴》原文断作五组,而是除了“平卢”之外,其余“淄青兖郓登莱齐”可分别划专名线,即表示“淄、青、兖、郓、登、莱、齐”等州;其次,李希烈所兼其实就一个藩镇节度使,也就是俗称的平卢淄青节度使,而其下辖有淄、青等州。第二点想要说明的是,在作者所讨论的时代范围内,藩镇体制尚未完全定型,无论是藩镇地域范围,还是藩镇名,都处在变化之中。藩镇名基本是随着藩镇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藩镇地域的变化,则取决于唐廷对安史之乱以及此后其他乱事的应对策略。因作者重在对应对策略的考察,即如何在面临危机时重构权力格局,故虽然对随之而来的藩镇地域之演变多有讨论,但对更进一步产生影响的藩镇名的演变,颇有遗漏。其实,藩镇名的演变,在安史之乱期间,一切都是出于平叛策略而定,故当时所命节度使多以地域名来命名,并取该地域中的治所州和其他重要的州作为这一新设藩镇的简称或俗称。而当各种乱事平定之后,随着各个藩镇辖地的渐渐固定,另外出于对跋扈藩镇的羁縻作用,和对顺命藩镇的激励作用,会赏赐各种赋予美好意涵的军号,作为该藩镇的正式美称,并固定下来。比如“昭义”,即表昭示忠义;“宣武”,即表宣扬武功等。作者谈到河南藩镇格局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前后全部完成之时,也集中描述了新设置的河南藩镇如义成(785)、武宁(805)、忠武(804)、彰义(798)等军号之赐予。(第98-99页)总而言之,通过对藩镇名和节度使名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藩镇从临时到固定的一个发展过程,从而在名号问题上确立了整个藩镇时代的格局。
第三,地名除了断句不同会造成混乱外,对固定地名内涵的不同理解和使用,也会产生一些误区。就李书来说,因为涉及到大量历史地理问题,对地名含义的准确定位,便十分重要。而在李书中的使用问题,主要是指古今地名的混用,以及对通用地名内涵的不同解读。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始于笔者对作者关于党项部落分布问题的讨论。在第二章中,作者引用了《册府元龟》的一段话,谓永泰元年(765)二月,“河西党项永定等一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公劳等一十五州,许之。”[20]作者在引用之后,又于脚注中写道:“‘河西’无疑指黄河以西,因此我推测此处的‘河西党项’当指陕北一带的党项部落。”(第121页)在这里,作者提到了两个地名:“河西”、“陕北”,亦即涉及到古已有之的地名“河西”的含义,和完全是明清以来方有的地名“陕北”。作者认为“河西”是指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又在其他行文中多次提及“陕北党项”(第120页),以及“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第121页),可见其将数百年后明清时期的地名概念等同于夏、绥、银、延、麟等唐代的州,并进而将“陕北”一词加诸于散处于这一地带的党项部落。
然而,就“河西”而言,此词内涵虽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唐代所指应该是河西节度使之河西,而非今陕西省和山西省交界之黄河中段以西。河西节度使的设置,本身即为了隔断吐蕃和突厥之间的交通。但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河西节度使兵力的内退,其地逐渐为吐蕃所侵逼,在此地的党项部落内属,自在情理之中。如果按照作者的解释,河西指所谓“陕北”地带,本身不在吐蕃直接侵扰范围内,又何必内属呢?而且,河西党项此前有永定等一十二个羁縻州的规模,内属后分为公劳等一十五个羁縻州,可知其活动范围应该经历了一次空间转换,并且藉此调整了部落数量。[21]若是在“陕北”地带,恐怕也不必如此费力。另外,作者所指的“河西”地区“陕北党项”,当指根据郭子仪(697-781)的建议从盐州、庆州等处东迁至“陕北的夏、绥、银、延、麟诸州”的党项。(第121页)然而盐州、庆州等地的党项,根据作者之前所引胡三省(1230-1302)注的解释,应该是早在贞观以后即存在的“党项拓跋诸部”,他们既然已经在此地生活了一百多年,又何必再次内属呢?所以,作者此处混淆了两个“河西”概念,导致对党项活动范围的误解。
此外,就“陕北”而言,作者多次在行文中使用此词,似不恰当。“陕北”之名,大概起自元代陕西行中书省设置之后。虽然作者在讨论时涉及到的鄜、坊、丹、延等州属于鄜坊节度使辖境,自成一个地理单元,且可以在地域上约等于今陕北地区。然而毕竟古今有别,今天的陕北地区有其具体的行政区划范围,贸然使用于讨论唐代历史的论着中,似非严谨。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作者其他相关讨论中,最明显的就是书题中的“帝国”二字,这虽非地名,却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并不适合用于讨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中。
三
虽然书中有尚待改进之处,但李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在此基础上,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只能从李书论述体系之外的层面加以考量。此外,结合笔者本人的兴趣,李书所涉及之问题中可以进一步阐发的,尚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兴理念的存在。
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王朝兴衰。由于王朝基本是一家一姓状态,在家族内部世袭,故而一旦家族传承中断,该王朝也就灭亡了。因此,历代王朝在遭受一次重创之后,都十分重视对于“中兴”的期待和书写。对于唐代的这种理念,往远了说可以追溯至“少康中兴”,近一些的榜样则是“光武中兴”。不过中兴也有分别,少康中兴、光武中兴可以算作本朝被他人僭取统治权几十年后,再次反正的现象,类似于唐中宗(656-710,683-684、705-710先后在位)的恢复大唐国号,以及后唐灭后梁后对唐朝国号的重拾;另一种中兴,则是本朝国势,特别是皇权一度衰微,但尚未完全亡国,此后经过数年努力,使国势重现光芒。前一种中兴,由于前后两个时段之间相隔较久,甚至可以目为两个朝代。后一种中兴因并未中断,故尚处于一个王朝之内。就唐朝而言,后一种中兴又可分为两类现象:一类是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长安被攻占之后,唐朝皇帝出逃数年,又返回长安并平定战乱;一类是对于藩镇势力的压制,从而得以再次伸张皇权,比如“元和中兴”。安史之乱是这后一种中兴的第一类现象;而唐德宗时期对藩镇的压制或可算作第二类现象,但不如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更具典型。
李书对于中兴并未具体关注,但由于所讨论的内容本身主要包含三次中兴(肃代中兴、德宗中兴、宪宗中兴),故而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唐人的中兴理念来观察唐后期的这类中兴现象。对此,以元和中兴的相关关注为最多,或者说最愿意把“中兴”二字摆出来。[22]当然,肃、代、德等宗也有自我而中兴的意思。对此,孙英刚关于唐肃宗通过无年号与改正朔的努力来塑造自己中兴之主的形象,已有较好的研究。[23]我们后来人需要更进一步阐发的,则是每位皇帝对谁是真正“中兴”之祖的认定,及由此而涉及到的对各位皇帝统治理念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两大类中兴,前一种接续中断之王统的中兴,可目之为“当然中兴”;而后一种在王朝统治遭受重创情况下努力追求重现辉煌的中兴,可目之为“主动中兴”。通过这样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何以唐中宗会禁言中兴,即对于大唐王朝来说,中宗反正是理所当然的中兴,但出于亲情,唐中宗并不想把武周与大唐截然分开。[24]而在安史之乱后的各位唐朝皇帝,则不存在类似唐中宗的顾虑,故而他们极力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祖,并积极追求中兴业绩,从而或多或少影响到藩镇时代的历史进程。
其次,行营组织的设置。
随着府兵制的日渐衰落,唐前期盛行的行军体制也不再流行,直至睿、玄之际节度使体制的起步,新的驭边策略,乃至战争动员机制开始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前,主要地处边疆地区的节度使,承担了唐王朝与边境诸政权的作战职能。随着战果的扩大,边疆地区节度使日益成为手握重兵的将领,严重威胁到唐廷的权威。最终,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应对,又将节度使体制扩展到内地。藩镇的普遍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也有分而治之的目的。不过这时已经无法行用府兵制和行军制,取而代之的便是行营制。行营的出现可追溯至安史之乱以前,但却在安史之乱期间从泛称转为专称。[25]此后,每当唐廷征讨某个具有不臣倾向的藩镇时,即会组织由其他各道或神策军组成的行营。
在笔者看来,行营有两类情况:一类是神策军在各驻地的神策军行营;一类是战争期间具有临时性质的行营。黄寿成对于河北地区神策军行营的梳理[26],以及黄楼和李书作者李碧妍对关中地区神策军城镇的整理(第209-248页)[27],都是前一类行营。目前关注较少的是后一类行营,李书虽然也涉及到,但并未深入。笔者曾就自己关注的时段唐末,探讨了唐廷镇压黄巢期间所设置的行营[28],晚唐在代北地区设置的代北行营[29],以及唐末唐廷征讨蔡州秦宗权的蔡州行营[30]。然而,对于晚唐时期其他时段的各类行营,尚需更多个案研究。就李书而言,作者在讨论关内振武军藩镇时(第129页),曾提及一段史料:“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31]这段话很好地传达出了后一类行营的内涵,即各藩镇出兵,由一人统领由诸道兵组成的行营。而当行营统帅被罢,则行营诸将也就回到原来所在藩镇,行营随之解散。在这类行营内部,行营的统帅和参与行营的诸道兵之间,以及与唐廷之间组合成的各种关系,就成为了我们观察当时(特别是战争期间)朝藩关系和藩镇格局的最佳窗口。
第三,藩镇时代的延续。
所谓藩镇时代的延续,不仅是指全国大部分地方在行政体制上以藩镇体制为主导,也指各地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上存在的藩镇思维。可以说,自安史之乱以后,开启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迥异于唐前期的“藩镇时代”。这样的一个藩镇时代,不仅在于藩镇数量和边界的日渐固定,也在于藩镇地域文化的慢慢形成。这一时代起始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终结于北宋最终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约有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而其中最为典型的时间段,即从安史之乱结束前后到王黄之乱的结束。王黄之乱的爆发,改变了旧有的藩镇格局,使得部分藩镇日渐走上兼并和统一战争的轨道,这不在李书主要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也暂不涉及。
作者在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中,已经阐发了藩镇时代所带来的两大影响:一是地方政策从“关中本位”到“中央本位”,二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第536-546页)在这两大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地方基层势力的崛起,这也是笔者想要强调的。对于典型藩镇时代的地方势力,作者在第三章对河北藩镇地区两种军事构造模式的区分,即为很好的研究。当然,无论是作者对于河北道燕南·燕·燕北的划分,还是边州、次边州和南部地区的划分,乃至对于“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的区别,都不可避免涉及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是在安史之乱以前即已存在,但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割据状态下被加强了。而这方面,陈磊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唐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和社会分群,惜作者未能就此文进行对话。[32]目前来看,虽然由于对藩镇个案的雷同性研究已经过多,导致大家深感疲惫。[33]但依然需要在更全面地借鉴和利用已有的藩镇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藩镇时代之下各个藩镇内部的具体动向,特别是地方势力的日渐崛起和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对后世的影响。[34]
以上,为笔者通过对李书内容的阐发,揭示了该书在研究藩镇时代启幕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启幕之后,是藩镇时代的具体展开,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已刊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第350-365页。
[1] 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关于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的学术史,分别参见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7-17页;胡耀飞:《百年来王黄之乱研究综述(附:王黄之乱学术史编年录)》,林淑贞主编《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21期,中国唐代学会,2015年12月,第69-107页。
[3] 相关研究史及代表性专着,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4] 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中译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中西书局,2014年。
[5] 李碧妍、仇鹿鸣座谈,王子恺整理:《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2015年11月21日。网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122
[6] 白居易:《长恨歌》,《白居易集》卷一二《伤感四》,中华书局,1979年,第238页。
[7] 于鹤年:《唐五代藩镇解说》,《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5期,1935年3月8日。
[8] 维舟:《另一种“唐宋变革说”》,《经济观察报》,2015年10月27日。笔者参考的是维舟自己在豆瓣贴出的网络增补本: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57544/,2015年11月13日。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卯条至十一月丁丑条,中华书局,1995年,第1568-1577页。李书引用《长编》此段史料时,脚注误作“卷90”(第34页)。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壬寅条至二月辛酉条,第1862-1865页。
[11] 以上意见和史料参考刘本栋在豆瓣上对李书的网络书评《“东巡”非“东封”:有关〈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一点意见》,2015年12月18日。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95793/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7302页。
[13] 河西走廊诸州陷落于吐蕃之手的时间,参见刘子凡所绘制的“唐朝西北州县陷蕃图”,氏着《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第321页。
[14] 福建观察使派兵支援朝廷平叛的情况,在此时虽然没有直接史料体现,在几十年后唐宪宗平定淮西吴元济时确有证据。根据唐末福建观察使陈岩(849-892)的墓志,陈岩曾祖父陈宏“为当府司马,时淮西逆命,帅军讨之”。其中所指,即陈宏作为福建观察使府行军司马,率兵参与对淮西的征讨。参见胡耀飞:《王闽前史:陈岩家族对福建的统治(884-893)》,第十一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2015年3月21-22日。
[15]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五九,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18页。
[1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页。
[17]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60页。
[18]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9页。
[19]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唐德宗建中三年七月条,第7333页。
[20]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门》,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82页。
[21] 关于关内道的羁縻州分布,郭声波有详细探讨,参见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65-1125页。但因为属于李书作者2011年博士毕业之后出版,故未能及时参考。乃附见于此,不做讨论。
[22] 李树桐:《元和中兴之研究》,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三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郑学檬:《“元和中兴”之后的思索》,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
[23] 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第65-76页。
[24] 对于唐中宗禁言中兴,亦可参考张达志的研究,因属未刊论文,故不便直言其结论。张达志:《唐中宗禁言中兴相关问题考论》,“中古新政治史研究”:第四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国际会议,上海师范大学,2016年7月23-24日。
[25] 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291页。
[26] 黄寿成:《唐代河北地区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85-88页。
[27] 黄楼:《唐代京西北神策诸城镇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1年,第346-380页。此文虽然版权时间为2011年,但直至2014年方才正式印行,故而该书作者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未能及时参考并进行对话,情有可原。
[28] 胡耀飞:《传檄天下:唐廷镇压黄巢之变的七阶段行营都统(招讨使)考》,纪念黄永年先生九十诞辰暨第六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10月17-18日。
[29] 胡耀飞:《从招抚到招讨:晚唐代北行营的分期与作用》,苍铭主编《民族史研究》,第12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211页。
[30] 胡耀飞:《从平叛到扩张:唐末蔡州行营的设置及其意义》,董劭伟主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5-80页。
[31] 《资治通鉴》卷二三〇,唐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条,第7409页。
[32] 陈磊:《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的文化分区与社会分群》,李鸿宾主编《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240页。
[33] 陈翔、秦中亮:《书评: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收入《陈翔唐史研究文存》,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84-286页。
[34] 对于藩镇时代的各类研究视角,笔者也稍有思考,参见胡耀飞:《论史念海先生对藩镇研究的学术贡献——兼论“藩镇时代”研究的历史地理视角》,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4-190页;胡耀飞:《书写童年:藩镇时代的儿童史研究引论》,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0-278页。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三):“东巡”非“东封”,有关《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的一点意见
近来有幸得以拜读大作《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深感李女史学术之精深,佩服至极!因我对宋史稍有涉猎,故就大作第一章第一节所引《新唐书?忠义传》”赞“中有关”章圣皇帝东巡“一事,稍作异说。
大作中将此事定为”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第33页),由此导出,宋真宗”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依据是大作第34页,注释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所记为天禧元年之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十一月之事应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第1567-1579页),就此推论出此“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只是欧阳修的“道听途说”(第34页)。如按作者的理解逻辑,得此结论完全没有问题。可遗憾的是作者可能存在将”东巡“误判为”东封“,换言之,就是将宋真宗东巡亳州祭拜老子与宋真宗东封泰山二事混淆为一事,将二者张冠李戴了。
宋真宗东巡亳州,亲到应天府一行记载,见于《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丁未、壬子、乙卯条,原文在此不再赘引。其实宋代应天府确实存在祭祀张巡和许远的庙宇,在北宋时,当地称之为”双庙“,有关记载见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祠庙事奏》“又有双庙,乃是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所谓能捍大患者”。此奏为张方平在判应天府时所上呈给皇帝之疏。故此可知,真宗东巡亳州时,亲到张巡、许远的双庙。欧阳修在《新唐书?忠义传》“赞”所说“章圣皇帝东巡”一事,应是在此时确曾发生无疑。
故李女史在大作中第33-34页所说宋真宗“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实际上也不可能经过)当时的应天府”,此话题的记载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只是欧阳修的”道听途说“的观点不成立,由此结论所绘出的真宗皇帝东巡地图也是错误。
最后申明一点,发此评论,并无他意,只是出于对李女史学术的敬佩,像《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如此上乘之作,如能避免这样的小小瑕疵,将会更加完美。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四):另一种“唐宋变革说”
平日惯用的朝代划分时常会误导人。尽管世人印象中的唐朝多是“盛唐气象”所留下的,但自安史之乱后唐代还有长达150年的后半期,而中晚唐这一时期无论在文化还是社会结构上来说,可以说都是“宋型文化”的一部分,与初唐、盛唐相比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这一点来看,中晚唐时代是宋朝的“前传”,宋代文明正是从这一躯壳中孕育出来的,不回到中晚唐是无法理解宋代的,而要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藩镇割据。 危机 对唐帝国而言,安史之乱是一次整体危机的爆发。就像后世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样,它虽然没有摧毁帝国,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原有的运作方式,人们被迫认识到:原有的老法子是不行了,必须找出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由于危机如此重大、所能采取的手段可能又有限,混乱、错误都在所难免,有时解决问题的努力却又引发了更麻烦的新问题,而原本只打算临时应对的举措或许就变成了长期政策,甚至为了避免局势更坏,也只能默认一些不那么坏的现状一直维持下去;与此同时则要竭尽全力挖掘新的机会与可能,调整权力结构以适应这一变化。 李碧妍博士在书中清晰地梳理了唐帝国这一危机下,中枢权力与不同地方诸侯之间的博弈。在全书一开始她便已开宗明义地指出:“假若我们将安史之乱看作唐帝国所遭遇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藩镇涌现的局面,仅仅是帝国君主盲目草创的一种产物,更不是为了在乱后寻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地割裂王土的结果。相反,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甚至还包括帝国前期痼疾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这在史观上已破除了传统上那种将中晚唐视为衰世、乱世,而藩镇割据是分裂混乱体现的正统观。确实,只有充分理解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才能解释宋代的种种特质与重现辉煌,也才能明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文明所蕴藏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虽然各藩镇都想要控制所属州县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都寻求某种自治和自主(突出特点是将帅、官吏自行决定,即《资治通鉴》所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但各地做法不同,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也因之各别。在这里,她并不是采取正统观下那样“中央=合法正统”、“藩镇=非法分裂者”的二分法,倒不如说是将他们视为平等的两个博弈主体和行动者(agents),双方在互相试探中不断寻求机会点,各自都想要实现自己权力目标的最大化,但同时又要将损失最小化,由此不断学习与调整,趋于一种“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谨慎小心地不断进行理性计算,尽管它们各自采取的言辞可能仍是高度程式化的王朝话语。 由于这种多重行动者存在,权力在很大程度是被分散化了,地方权力上升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和晚清时一样,对中央权力的攘夺不仅来自叛乱一方,还来自号称是忠于王朝的一方,因为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局面中,中央不得不放权给地方,由他们见机行事,因而安史之乱期间玄宗便已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这样,一如韩升在《盛唐的背影》中所说的,“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 毫无疑问,支撑这种分权局面最根本的是独立行动的军队。中晚唐时期屡屡造成危机的正是种种不服中央控制的军事力量,那也是藩镇割据能得以维持的根本——正由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因而最终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上也是依靠军事征服、或至少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收服。宋代“强干弱枝”、将力量集中于中枢禁军、两宋之际对岳飞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将领特别提防的原因,恐怕都可追溯到这里。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因而在这种军事割据局面背后的则是财政危机和税收体系的重组。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但李碧妍并未展开讨论。概括地说,政治和军事形势上的危机造成了国家财政结构崩溃,由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土地分配制度也不再起作用,因此,对割据局面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亟须改组地方行政结构、加强对财税的挖掘和汲取能力,以强化自己的军事机器。在急需军费的惶急中,各地军政长官以任意名目摊派,造成极为紊乱的赋税制度。正因此,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认为中晚唐“财经制度亦有很大的变革,其变革幅度之大,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在基本上,这些变革,都是对当时问题或挑战的响应,譬如面临安史之乱,庞大军费无着,不得不整顿盐政——后来,宋代亦利用盐政,解决军粮运输问题;代宗因奔陕州,陆运所费不赀,不得不改革漕运;由于支出浩大,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从而演变为两税制;中唐以后,商业发达,对钱币需求增加,因币材供给有限,以致出现飞钱;北宋平蜀后,蜀人因铁钱不利于流通,乃创出交子。”众所周知,南方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税中心南移,而为了强化这种财税输送并保护、扩大税源地,朝廷才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此外,朝廷为筹措军费还加大对富商索取的力度,征收商税,德宗建中二年(781)便“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甚至连僧侣也不能免于榨取,“安史之乱中,朝廷以出售度牒来筹军费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见《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 凡此等等,皆可见帝国为了应对危机,是如何想尽办法地开源节流。而这些做法,与近代西欧各国几乎如出一辙。变革,往往都是这样被危机逼出来的。无论过往“唐宋变革说”的立论点如何,那说到底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应对一场全面危机带来的挑战,中国不得不对在社会、财政、军事组织、行政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构 对不同藩镇案例的分析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李碧妍在仔细深入讨论之后令人信服地证明:朝廷与藩镇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具体状况和权力结构。在河南藩镇,是通过分割原先平卢系军阀的政治版图并瓦解其军事支柱,使之重新接受唐廷控制;在关中和朔方,逐渐在禁军的控制下实现军权的集中化。最复杂的则是河北藩镇:安史旧将控制的成德镇在确保其世袭特权的情况下,与唐中央反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关系;以难以控制的地方职业兵(牙军)主导的魏博镇,则屡屡发生权力更迭;辖境最稳定的幽州镇,则内部变乱频繁。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河朔三镇当时其实经历了一个可称为“再封建化”的过程:藩镇统治者视唐廷为宗主,而其内部将士、人民则又视他们为宗主,但在这一封建分权体系下,“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 如果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路径,或许可以说,在经历中晚唐的危机之后,重新统一的宋帝国已蜕变转型为一个新型的、早熟的“绝对主义国家”。佛教寺院、地方藩镇均遭到沉重打击,979年北汉的垮台意味着中原再无封建力量能对宋朝中央构成挑战,正如勃艮第家族的败亡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法国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何宋代之后再无藩镇出现,因为一个重组后的中央权力已不再与地方精英分享军事权力——晚清民国的军阀局面与帝国中央权威崩溃的进程同步,这大概并非偶然吧。 当然,历史发展的结果,并未像西欧和日本那样将这种分权自治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和固化,而是激发了中国社会内部寻求重新整合的力量——这一过程,李碧妍称之为“重构”。这种“重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行政体制、财税制度和社会构造上,虽然她也注意到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都改变了,不过正如她在分别剖析藩镇案例时按地理版图的划分一样,她在理解这一重构进程时侧重的还是某种空间的视角,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唐朝从前期的“关中本位政策”转向了“中央本位政策”。具体地说是“一个国家从各个地域相对独立,唯政治中心所在地更为突出的地缘结构形态,向各个地域相互依赖,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功能差异的地缘结构形态转变的过程”,“至于藩镇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它见证了帝国从区域本位向中央本位的转变”。这也开启了宋代那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强本弱枝”为主导思想,宁可放弃边地来巩固中央权力。 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她作为周振鹤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历史地理学取向,而非采取历史社会学的进路来讨论这一问题。她也并未使用社会学那种建立模型的方法,但较之原先的历史地理学则丰富多了,尤其是特别强调“结构”,从而突破了原先那种认为唐廷与藩镇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传统视角。 斗争 如果转换成历史社会学的思路,在我看来,那这段历史差不多是Richard Lachmann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的典型案例,其历史走向取决于不同精英群体(代表唐廷中央的皇帝、宦官、贵族、官员等,与代表藩镇的节帅、骄兵悍将)之间斗争的结果,最终产生的新局面是不同行动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可能是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博弈并不只在中央与藩镇之间展开,中央内部的皇帝与宦官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将领与将领之间、乃至将领与牙军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斗争,有时又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可以暂时结盟——例如藩镇之间虽然也争夺领地,但在面临中央讨伐时,则互相依托纠结,共同抵抗。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当时存在着某种双重的权力关系:对郡县制下的官员和人民来说,虽然他们也效忠于皇帝,但更多总是一种“国家-地方”关系;但在安禄山、史思明乃至藩镇节帅的心目中,权力关系或许更多带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庇护-追随者”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就像早先边地各族所用的“天可汗”一词所标明的那样,他们对中央的顺从,本质上是对皇帝个人的追随,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层层的政治权力庇护关系,而非去个人化的抽象国家权力。 李碧妍的分析中,着重的是各藩镇的行动,但这局面中最大的主角还是唐廷,因为它与所有藩镇都进行博弈。复杂的是,唐廷自身内部的权力也并不集中,唐帝与宦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关系,皇室得靠军队支持,但禁军兵权却掌握在宦官手中,而宦官又是以皇权的名义掌握兵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皇帝借助方镇兵铲除宦官,与罗绍威借朱温军铲除魏博牙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借助外力解除了内部威胁,但自己也由此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这一点上说,唐帝与藩镇的权力构造是同构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很多应对措施也正是“总结经验”的结果。宋代甚至解决了唐皇室与宦官之间的棘手关系,禁军自此不再掌握在宦官手里;通过“杯酒释兵权”,不动声色地而又温和地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可能是科举制度,它不仅使得官员权力去军事化,而且从社会普遍选拔的科举人才远比独立性较强的贵族及藩镇听话——虽然士人会向皇帝进谏,但他们不构成一支独立行动、并能威胁皇权的封建力量。其结果,宋代的君主专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峰。 对朝廷来说,手里还掌握着几种特殊的武器,尤其是作为合法性的源泉。宦官虽然能任意废立皇帝,但仍须借助皇权的名义;藩镇虽然抗拒王命,但其权力却不能仅靠武力。《新唐书》卷一四八记载,史孝章流泪进谏其父史宪诚说:“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史宪诚父子本身就是奚族,是“夷狄”,史孝章却显然认为河北藩镇被天下视为胡化的化外之地是可耻之事、藩镇“挺乱取地”本身不合法。仇鹿鸣在《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中晚唐的中央与地方》一文中已论证:藩镇实际上仍不时需要借助唐廷来赋予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 借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从“强国家”(strong state)转向“弱国家”(weak state),中心被动乏力,而地方和边缘却积极活跃,这样,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目标被迫转而由一个网状、多权力中心的社会来实现,但矛盾的是,这一社会结构又为动员人力物力资源带来极大限制,而为了实现稳定,这种动员却是必不可少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便是李碧妍所分析的,在理性算计之后达到一个低成本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在与藩镇的斗争过程中,帝国中枢权力追求的是在这种“横向权力结构”(表面上藩镇臣服,但拥兵自立而为相对独立的行动者)上,试图终结藩镇在地方上的霸权,从而走向“纵向权力结构”而造成一个绝对主义国家。 在这一过程中,唐帝国中枢权力所能采取的策略手段可以灵活多样:在藩镇薄弱的地方使用武力(浙西镇)、对安稳的地方予以收买(成德镇),对叛服无常的魏博等藩镇则恩威并用。由于国家的策略重心是打击妨害自己权力向下贯彻的封建巨头,因而更注重拉拢更下层的精英,他们往往更乐于效忠于中央,这既使国家权力向下渗透,但又要防止这些人被挡在朝廷的机会之外而产生怨恨,主要从下层精英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在中晚唐、尤其是宋代之后得到大力推行,大概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也解释了本书末尾所说的,唐代后期打压地方豪强效果不明显,政府对是否打压也顾虑重重,这的确是因为“唐代后半期国家的正常运作已越来越要依靠土豪层的支持”,但值得补充的是,这本身也是中央拉拢地方豪强来打击藩镇这类封建巨头的结果,麻烦的是,这些土豪的数量又太大而无法完全收买。这些底层精英正是宋代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特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开创了宋朝。 原载2015-10-27《经济观察报》,现有增补 ---------------------------------------------------------------------------- 勘误: p.233:贞元时代出现的以神策军为主导,并逐渐临驾边军:凌驾 p.287:如果说,安禄山的价值观还是侵润着东北边境独有的种族文化特质的话:浸润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五):李碧妍前辈学者做过的选题,年轻人还敢选作博士论文吗?
来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852 觉得对研究生的选题有些启发,帖在这里。
我从大三开始做唐代藩镇的研究,当时对藩镇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后来的研究中我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启发,累积起来才呈现出这本书现在的样子。
这本书最早完成的部分是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中的《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那一节。那时候我正在读大三,当时有个契机,是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有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就是韩滉的《五牛图》。后来在完成“隋唐历史与文化”专业课的作业时,我打算写唐代中晚期南方社会经济的问题,看史料的过程中发现韩滉这个名字很熟悉,回想起来他是一个画家,才知道他其实是唐代历史上很有名的节度使。这就和我们常识性的观点有差异:谈到藩镇时我们往往先想到河朔地区桀骜的北方藩镇,不会想到南方其实也会出现强藩,南方藩镇的节度使也会对政局产生大的影响,这就促使我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非常幸运的是,在研究韩滉这个人物时,你会发现史料中关于这个人物的记载很微妙,但这种微妙又不像两《唐书》记载的张巡那样有显著的差别,而且不同史论对韩滉的评价也判若两人。这些问题对于大三时刚开始学习论文写作的我来说是很困扰的,再加上当时的历史基础也薄弱,不过我很感谢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一则他还没有被别人系统研究过,不管我研究得如何,我都可以尽自己所能去感觉和发现一些问题,没有什么已有的研究思路会框缚我(当然,也因为如此,一开始的研究是会走一些弯路的)。另一方面,也正是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在我刚开始研究生涯的时候,我对文献就产生了一种敏感,非常注意文献彼此间叙述语句细微的差别,而唐史的研究是有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包括《文苑英华》、《全唐文》或各类碑志、笔记小说中的资料可作比较的,这是研究唐史的一个先天的优势,也影响了我个人写作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我基本不用孤证,所以如果我发现史料之间有些有叙述上的出入,包括叙述语气的不同,我就会特别留意,而且在研究中基本我都会追溯史源。这种写作方式当然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但确实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所以一个研究者倘若能遇到一个好的研究对象或课题,其实是很幸运的,作为研究者,并不总是我们在操作或成就研究对象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韩滉这个人物,因为他成就了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思考问题的一些方式。
在写完有关韩滉这个人物的本科毕业论文后,我的硕士论文很自然就想写韩滉所在的江淮地区的镇海军这个藩镇。于是我开始关注韩滉的后任、另一位重要的浙西节度使李锜叛乱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插曲,我在暑假写完初稿,放了两个月,又花了两三个月陆陆续续改了五稿,基本利用了所有现存有关李锜一事的史料。后来有次想查《唐研究》某一期中关于浙东节度使薛兼训的残志,突然发现陆扬先生几年前就已经发表了一篇有关李锜叛乱的研究论文。这一惊不小,因为我原以为像韩滉一样,没有什么人会研究李锜这个南方藩帅的。读完全文我当时是更加绝望了,我觉得李锜事件被陆扬先生写到这个份上,我这篇文章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呢。
当然痛苦归痛苦,毕竟已经定好了硕士论文的方向,不能不写啊。于是我就分析陆扬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在李锜和中央的关系这方面,我能想到的陆文都想到了,我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还有些地方是读了陆文后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写作空间了。但是我的文章着力关注的李锜手下的军团构成问题,却是陆扬先生那篇文章不需要关注的一个层面。于是妥协的结果就是,我得再充实后者,而前者当然不能不碰,因为这个事件所反映的李锜和中央的关系必须作为背景有个交代,那我就主要引用陆扬先生那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吧。后来回过头来看,这真的是继韩滉一文后又一段很宝贵的写作经历。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大家的研究各自的点都很小,彼此对话的机会其实是很小,有些甚至是很有限的,因此当你遇到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鼓励你学习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大约四五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导师周振鹤先生在出差日本的时候遇到了陆扬先生,就把我的文章请他评阅,那时我已经读博士了。陆扬先生当时又指出了几个我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这之后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又进行过几次交流。你会发现,两个人用同一批材料研究同一个问题,但切入的视角不同,看到的面向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对方疏忽的一些盲点,而经过这样的写作,李锜事件本身的面貌却因此越来越清晰和全面了,对研究本身而言,这必然是一个进步啊。
事实上在我此后的研究过程中,比如奉天之难、神策军、河朔藩镇、永王之乱等,你会不断遇到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你会越来越发现这真的不是一件可怨的事情,恰恰相反,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这些先行研究不是你研究中的路障或跨不过的里程碑,它们是一个平台,帮助你得以站在他们的肩上看到一些更远的风景。而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说,我是比较喜欢有前辈学者带一程的研究方式的,就好比你小时候去的那些公园,我的研究风格是我不会选择大家都会走的那些公园主干道,虽然那里有公园最显豁亮丽的风景,但人很多比较闹,我会选一些小路去开辟或领略其他游人不太关注的别致小景。但是,这不是说主干道是无用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你才不至于迷路或走歪路,而且当你领略完曲径通幽处的风景再回到主道上时,整个公园的丘壑走势、景致安排就能了然于胸了,那个时候的你心胸一下子就变得开阔了。因此你说你能不感谢这些前辈学者的优秀研究吗?
回到写作的过程上来,我觉得做研究要做有延展性的课题比较好,比如本科写一个人物或一起事件,硕士写一个藩镇,博士写一群藩镇和一个时代,这样一点点学习,从小到大地驾驭,知识基础、史料文献也会打得更扎实一点。这中间,我很感谢荣新江老师的《归义军研究》这本书,我觉得研究者如果要想写好一个课题,不妨在刚开始时选一个和自己的研究理路、对象比较相近的一本优秀作品作为范本来学习。我写镇海军的硕士论文时,在规划布局论文结构的时候就是学荣老师这本著作的。虽然很多人会把这本书当作敦煌学研究的典范,但在藩镇领域,这绝对是我迄今读过的最优秀的藩镇个案研究了,主体结构和细节考证都很精彩。当然,通过之前这些学习研究的经历,我个人也逐渐发现自己的研究特长在政治史领域,逻辑推理和对细节的敏感是我的长处。我觉得做研究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性格特质契合的研究路数,比如有些研究别人做得是很好,但这种路数或这个领域不适合你,你学不来的,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个研究者若能发现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研究,有时候比你研究做的究竟是什么更重要,因为只有扬长避短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
就好比后来我进了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读博,起初我是不准备再做藩镇研究的,因为之前我所做的藩镇研究是以时间为线索,是纯政治史的研究。当时为了使自己今后的博士论文更像一篇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专业论文,我最初选择的博论方向是唐宋时期的镇戍研究,准备做唐宋时期基层军事、行政区划,这也是历史地理学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其实当时也已经搜集了不少资料,开题报告和中期考核也都通过了。但坦率说,制度史和宋史的研究并不是我的强项,心里更想做的还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但又担心这和历史地理方向有出入。其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老师把我之前写的藩镇的文章推荐给了陆扬先生,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但陆扬先生读过我的文章后却是建议我一定要继续走藩镇研究这条路。这当然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很犹豫的,毕竟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了。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最恰当的时间遇到最恰当的人,如果改换一下套用在我的博论写作过程中,那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了最需要的书。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让我彻底下定决心依旧走藩镇研究之路的一本书——李峰先生的《西周的灭亡》。我当时一开始读这本书就被它吸引了,不仅是它的内容非常完整生动,展现给了我一副相当精彩的西周政治生活面向,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关键是整部书对各种类型材料的结合运用,尤其是结构逻辑、写作方法、问题意识都非常契合我的研究理路。其实在刚读完李峰先生的序之后我就被感动并有点开窍了。继续往下读的过程,感情是很纠葛的,一方面你觉得它写得很好,你很想学,而且你已经感到藩镇研究似乎也能写出这个味道,并且就像这本书一样,能将政治问题和历史地理结合得很好。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你已经定了博论题目,已无改换选题的可能,很难过。于是就这样纠结了一阵子,终于有一天我对自己说,与其这样纠结,留有遗憾,那还不如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写呢。于是我花了两三周的时间读史料,准备先从安史之乱开始时的河南写起,于是就写了张巡的那篇文章。其实写完后,包括对河南史料的爬模,我基本上已经有信心把河南的问题梳理清楚了。再加上之前已有江淮的研究,虽然当时关中、河北的情况还不清楚,但至少我心里已经不怵了。
于是那天我拿着张巡的文章去见周老师讨论换题的事情,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告诉周老师我想换题以及换题的原因,其实只讲了半小时不到,但周老师听完后是非常支持的,并且告诉我,对一个博士生来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研究问题,就要努力把这个问题做到最好,假如你都没有做好的信心,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来研究这个问题呢。那次谈话结束后我的心情真是一下子豁然开朗,相当开心,以至于我坐电梯到光华楼一楼,走出去看到外面下着大雨才想起把雨伞落在周老师办公室门口就这么出来了。后来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把四章正文、一篇附录、一篇代结语写完了,绪论部分中的综述在硕士论文时就差不多写好了,增改的地方不多。
所以说,做研究的过程有时真不仅仅是写一个题目、作一篇论文的问题,它是一个在你与史料、研究、周遭学人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塑造与提升自己性格,当然也是各种因缘际会与体会人生美好风景的过程。其中的开心与难受,与写作时的兴奋或压抑一并构成了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和回忆。这些都是值得珍视和感谢的,而这些都是多年来一直进行藩镇研究所回馈给你的,因此能找到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
其实现在可以跟仇鹿鸣老师说一件事,就是他在刚开始介绍时说我的书中有一处引述了他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那次闲谈实际上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读到我硕士论文中写的“刘展之乱”那篇文章时给我提出的评阅意见中写的话。这篇文章后来就是参考了仇老师的意见,经过大的改动发表并成为博论和本书中现在的样子的,而这个事情同样是发生在我准备更换选题的那段时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仇老师也是促成我最终能写出《危机与重构》这本书的鼓励者之一。所以在这里也要谢谢他。
我的这本书有一个主标题和一个副标题,副标题叫“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顾名思义说明我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藩镇。而从主标题“危机与重构”来看,这本书是有比较强的问题导向的,正因为我刚才说的,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些与常识性认识不一样的现象,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定式化的理论都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比如安史之乱,你可能也要对它的一些固有观点进行思考,我们长期接受的诸如反叛、异族和汉族的对立等范式都要不断反思。比如,藩镇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骄横跋扈呢?我在研究藩镇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就是仇老师说的,如果安禄山叛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藩镇是把唐帝国带向没落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还能有这么长时间的生存?另外唐朝灭亡也不是亡于藩镇,而是亡于黄巢起义。所以我就开始思考安史之乱究竟给唐帝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个主标题也是可以适用于很多时代、很多情况下的,宋代、明代也可以用。所以在这本书中你就要写出,从藩镇的角度看,唐代的危机是什么?怎样重构?它的危机与重构的特色表现在哪里,或者说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藩镇时代的特色表现在什么方面。至于研究的角度,由于我博士读的是历史地理学专业,所以第一反应想到的首先是要把藩镇的空间结构体现出来,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一个层面。而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本科、硕士做的都是唐代政治社会史的研究,所以除了空间结构外,我还想展现出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六):细节 细节 细节
先说四大优点。一。作者以安史之乱为中心,将中晚唐的历史时段尽量拉长,分区域进入历史细节,考证严密,发覆深刻,颇多创见。一。对历史细节发生的具体时间、空间的敏感让人钦佩。一。在关注历史细节的同时对全局动态的把握尤为难得。一。史料爬梳精细,洵为勤劳之作。
不得不承认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大部分时间眉头是皱着的。这书行文有些繁冗,很多可以用一两句话带过的地方常常是大段大段迂回的分析而偏偏没有那句切中肯綮的关键句。将全书字数控制在现在的三分之二应该会更好些。同时,作者的行文风格非常像日语。即,喜欢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后。这可能是作者的个人习惯或偏好,本无可厚非。但是,将对细节的淋漓尽致地发掘和把结论放在最后的习惯这样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带给读者的可能就是云蒸雾绕,迷失在对细节的考证和发覆之中。
作者无疑对于历史细节的可知抱有强烈的自信。这一自信在对细节的挖掘和考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在严丝合缝的以果溯因的推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立足廿一世纪观察八、九世纪,我们不知道的可能比知道的更多。当书中以果溯因的推理不断呈现严丝合缝的面貌时,我不得不开始注意到这种严丝合缝的不寻常。的确,严丝合缝很有说服力,但是过于频繁过于完美的严丝合缝让我觉得有些不自然。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理该如此’,不存在偶然,不存在廿一世纪对八、九世纪一些事情的不可知。于是,唐廷就被描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近视眼’,完全没有延续近三个世纪的帝国政府应该具有的起码远见。
在看似严丝合缝的以果溯因的推理中,我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同一个因在不同事件中产生不同的果,有时候这些果可能彼此南辕北辙甚至自相矛盾。这给作者在推理中提供了更多回旋余地,而且似乎也验证了南橘北枳的辩证法。但是这个度不好把握。比如,天气预报要是说:由于本市受暖气团影响,明天最高气温,浦东14.7度,思南路15.1度,徐家汇14.9度,那我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天气预报说:由于本市受暖气团影响,明天最高气温,浦东14.7度,思南路零下14.7度,徐家汇147度,那我是不能相信的。当同样的因被用来解释过于不同的果时,这些推理的说服力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作者以权力结构为切入点对历史细节展开挖掘和考证,并以权力结构来分析中晚唐政局和军力的博弈与变迁,爬梳精细,创见颇多。当然,也有不足。
++++++++++++
以下是我自己的瞎想,与本书无关。
所谓唐宋变革的变革到底变了什么革了什么?变革程度又如何?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它的不间断性上,唐宋的不间断性与唐宋变革如何共存?历史的惰性有没有让唐宋变革成为不可能?而fernand braudel 在 civilisation mat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第一卷中论及的 les structures du quotidien 真的在宋代发生了变革吗?如果没有,那么唐宋变革是怎么发生的,存在于何处?如果不谈唐宋变革,宋史专家会不会比较没有地位?进而,唐宋变革的提出会不会变成了宋史专家的谋\生工具?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七):旧瓶新酒透深意
近百年来,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古代史学界影响深远,内藤湖南认为唐宋之间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古”与“近世”的分界线。支撑内藤湖南观点最成熟的莫过于“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宋代经济的巨大发展。而这一切作用于行政制度上的变化莫过于政区沿革。唐代的政区划分基本沿用了州县制,而宋代虽然沿用州县制,但是形成以安抚司管军权、转运使管财权的兵、财与行政分治的复合型行政规划。之所以让兵权、财政与行政权分离,其主要诱因来自于唐代中后期一百多年藩镇割据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最终的结果,也导致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局面。 探讨藩镇割据的研究是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之前成果繁多,如何能在老树上发新芽,李碧妍博士的这本《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让人眼前一亮。本书选取了河南、关中、河北和江淮四个地域来研究藩镇之间的动态关系。这四个地区正巧反应了唐宋之际,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唐代后期经济重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淮,但是关中实力尚存,江淮更为富庶,河北毗邻北部边陲,旧有“安史之乱”之余部,后有契丹沙陀,此处已形成“魏博”等长期藩镇格局。只有河南早已凋敝,于是这里成为了多股势力角逐之地。同时,藩镇割据又是地方性武装夺权的政治产物,藩镇在下属将官的选择中,又颇为器重本地人。故而藩镇割据时期,无论藩镇还是直接服务于朝廷的各派势力其地方色彩皆甚是浓厚。作者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后,朝廷派遣担任河南巡抚中历任巡抚的祖籍,挖掘出河南地区微妙的势力纠葛,从而通过这种对史料极其敏锐细致的考察,分析出背后唐王朝对河南地区行政规划布局的重视程度,此种活用研究方法的技能值得称道。 近年来,周振鹤先生及其弟子在上古、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着卓越性的突破,本书的意义在于动态的看待山川地理与政局沿革之间的互动。周先生曾经在《体国经野之道》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政区规划的两大原则分别是“山川形便”与“犬牙相人”,在轮廓上“山川形便”是方便管理,在细节上“犬牙相人”是为了方便相互制衡。作者通过分析四大地区藩镇割据的动态行政区域变化来彰显“犬牙相人”的锐度,这一点深刻的影响到了后世行政规划制度的改革。使得全书名义上是通过分析藩镇割据来探讨唐代灭亡的旧题新议,实乃是分析唐代中后期行政制度的动态发展,探究宋代行政制度的变化内核。这是之前纯粹的政治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璞玉。 (本文荣获首届“芬芳四季 阅读中国”微书评大赛大学组一等奖,该赛事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7月举办,赛制要求书评作品需在1000字以内,本文为997字。)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八):隐藏在文字下的汹涌动力——马伯庸评《危机与重构》
作者:马伯庸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762223/answer/13799877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直接引用一段周振鹤先生的序言吧。
“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是作者多年来独立思考唐朝藩镇问题的心得总结。此书集中讨论了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唐代的地方政治问题……有别于以往的一些藩镇研究,本书作者的着力点在于将一系列被以往研究所忽略的藩镇事件,还原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场景之中;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界限内,去对与藩镇有关的各种地方政治事件进行阐释,以此来为读者展现一个富有生机,且呈现出多棱面的藩镇群体……
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敏感,并且也乐于在追索历史细节的过程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在逻辑推理方面的能力,因此阅读本书似乎有着面对推理小说的感觉。当然,作者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纠结于个别的历史细节,或只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有兴味的解读。本书作者的目标,显然是希望通过藩镇这一视角,去思考藩镇所处的时代的整体结构与发展方向……换言之,作者对藩镇个案的微观考察,希望最终导出的是对一个宏观时代的把握。”
诚如周先生所说,这本史论读起来有一种推理小说的感觉。(尤其是对我这种外行人来说)比如说吧,针对“张巡守睢阳”这个著名历史事件,作者别具慧眼地把它放在更大的视角里去看待,抽丝剥茧,从河南节度使这条线追查下去,发现河南局势与朝廷内斗相关,进一步引申到玄宗与肃宗的斗争,与朔方军的合作与分化等等。张巡守睢阳,只是这一系列高层斗争延伸到基层的一个悲剧——如果要把睢阳之守写成小说的话,从这个角度切入,一定会让读者耳目一新。
再比如说,作者在写神策军时,一度苦于无从下手。她自叙说:“我实在没办法,百无聊赖地在地图上拿《通鉴》里的那条元载和鱼朝恩争夺神策军镇的史料来标记,这是有关中晚唐神策军镇的一条重要资料,之前的学者都用过,这条史料里出现了将近10个神策军镇的名字。真是不画不知道,一画突然问题就出来了,我突然发现神策军的几个据点都集中在西面的凤翔一镇里,而且分成三排排列,我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了。其实也很明显,这三条平行线就是三条交通路线,这些神策军镇的分布全部在交通枢纽上。” ——作者遂抖擞精神,以此入手,从神策军的空间变化,考察了异族威胁和唐廷应对变化的情况。这是把开脑洞的技术,应用到了学术中去。
对于这些研究在学术上有多大的价值,我没资格评价,但我能从这些细致的考察和推理中,感觉到一种隐藏在文字下的汹涌动力。这动力充满戏剧性,是写作的绝好素材。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读历史论文的原因:它们能从耳熟能详的资料里开出别样的脑洞,这脑洞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方法论支撑,显得格外真实。
开脑洞也要遵守基本法啊。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九):仇鹿鸣、李碧妍:安史之乱为何没有导致唐朝灭亡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122
仇鹿鸣: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所谓封建社会前期向封建社会后期转变的一个关节点。而在最近几年对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乱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许有人已经留意到,广西师大翻译出版的日本讲谈社中国通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这一系列历史变化追溯到安史之乱,把它和辽金等从中国东北发源的政权对传统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战放在同一个脉络之下。去年在复旦的会上邓小南老师也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她说最近美国汉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从安禄山到朱元璋(姓名开头的字母正好是A和Z)构成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些观点都很有意思,它们都认为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无疑在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唐宋变革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唐朝从前期的开放包容,慢慢到后来强调夷夏之辨,慢慢趋向于保守,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走向。
所以无论在哪一个研究的脉络中,都会把安史之乱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安史之乱这个事件本身没有足够好的研究。
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有一处引述了我在一次闲谈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学术脉络中,关于安史之乱本身的过程缺少充分的研究。当然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记得在近十年前,陈尚君老师就在一次闲聊中问过我,说唐代历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细致了,在安史之乱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比较好的博士论文把这个事件讲清楚?当时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回应,只能举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当然我清楚这本书虽然经典,但限于篇幅和议题并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乱这一事件的主干。
在这样的研究脉络之下,可能出现一种遮蔽:我们都认为这个事件很重要,对这个事件的性质有各种各样的判断,但都没有详细探讨过这一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到底为什么重要?缺少细节的论述。当然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历史研究中“以论带史”倾向的影响,我们更重视回答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要对它的性质做一个判断。但坦率地说,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往往是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上,因为我们已经知晓了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它改变了历史走向。
但是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呢?比如我们一般认为,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黄巢起义的冲击,但是黄巢起义在开始的时候规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内部也没有风雨飘摇的感觉,所以我们对历史性质的判断,往往是带有主观立场的“后见之明”。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历史学需要揭示丰富的细节,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可能,以此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而不是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去研究它。
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现了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唐王朝面对安史叛乱危机及其衍生出来藩镇问题时的应战。一个王朝是不是强大,不能只看它强盛的时候,还应该看它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能不能很好地应对。在这个意义上,唐王朝是非常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之后,又重新恢复生机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爆发1260年整),唐朝灭亡直至公元907年,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还要更长一些。这样来看安史之乱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件。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作者。
李碧妍:谢谢仇老师的介绍,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这本书集中讨论了8世纪至9世纪初唐代的地方政治问题,四个章节分别论述四个区域:河南、关中、河北、江淮。
平定河南藩镇的策略
第一章是“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其中有些藩镇,比如宣武镇在中晚唐就很有名,五代的朱温最终也是凭借宣武统一北方大部的。但它们其实都是很晚才成立的藩镇,比著名的河朔三镇都晚,更不用说和安史时期的幽州等开天十节度相比了。这就迫使我在研究初始必须找出这些河南藩镇的源头,而一追溯就追溯到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节度使了。
然后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事实上研读史料我发现河南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时间是公元756年,因为面对安史之乱河南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地方,但史料中对于河南节度使的信息却很模糊,而且很快它就没有了。这就又使我思考一些和常识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史书或史论中会花很多笔墨写张巡等人在河南抵抗安史军队的事迹,但反而对真正应当肩负起抗贼大任、地位远非前者可比的河南节度使却没有什么记载?张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官,而且是出于一种爱国或忠义的热情来抗贼的,但这实际上却并不是需要由他来担当的一份责任。
按理说安史之乱期间双方统军的将领不应该轻易更换,但是唐朝方面的河南节度使却是不断在变化,背后肯定有原因。我意识到唐玄宗的统治策略在不断发生变化。一开始他的人选是张介然,他原来是西部军团中负责后勤保障的一个人物,在节度使军队中后勤保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和好几任西部军团的首领关系都很密切——因此玄宗的这个举措目的就很清楚,他想借用西部军团中的重要人物来抵抗安禄山叛军,但他没有想到失败得这么快。后来玄宗又想把宗室的一些人扶上去,这也是可以想到的策略,但这个人选牵涉出了玄宗和肃宗父子的矛盾,结果出现玄宗立了一个、肃宗立了一个,两个节度使并存的局面。而这场宗室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张巡抗贼的效果,回过头来看确实造成了一个悲哀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会议论张巡守城时发生了吃人的事情,我认为这不需要多谈是对还是错,而是应该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发生。
这样,河南节度使的变更就和安史之乱联系起来了。虽然张巡战死、河南节度使瓦解,但安庆绪也退回了河北,双方都回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战时体制下,继河南节度使后设立元帅、以河南为基地对抗叛军也是必需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实权的元帅人选也在不断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唐朝还是要选择西部出身的人物作为主导,只不过这个西部军团已经不是河西、陇右的军队,而是朔方军的统帅了,但它也不是朔方军核心的军队,虽然派出了李光弼这样厉害的朔方军前任领导,但他手下的军队并不是最主力的朔方军,这牵涉朝廷对朔方军的压制问题,以及河南毕竟不是平叛的主战场,这就自然地和黄永年先生以前的研究联系上了。
而在河南,如果元帅手下的军队是类似于张巡这样涌现出来的地方义军,那他们的实力毕竟是有限的,要和安史叛军这样强大的正规军对抗还需要其他力量的介入。而正在这个时候,安禄山的根据地出现了异动,北边的平卢军被史思明打败,只能渡海逃到地缘接近的河南地区。而对唐廷来说,当然也希望借用这一支同样出自东北地区的劲旅。但既然要借用就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而正在这个时候,元帅手下的那些原来的实权势力,虽然在战时成为对抗史思明、安庆绪军队的重要力量,但等李光弼这位战时最后一任河南元帅死后,这些实权人物的力量变得分散了,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唐朝政府打压了,比如地方将领的实力没有了,而原李光弼手下的嫡系军队也被唐廷调离河南了,那么北方来的这些平卢将领和军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继续安置在河南地区,填补河南的政治真空。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南地区的藩镇基本上就是这样由北来的平卢军建立起来了。
但等到平卢军势力站稳脚跟后,在平卢系藩镇和朝廷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彼此为争夺话语权、继位权的挑战,一直到德宗时期发生的著名的“四镇之乱”,我们可以看到唐朝非常希望借助藩镇内部的变动,把一些亲近王朝的人派到河南去,把以前那些不服从的力量磨灭掉。当然在这个磨灭的过程中,唐朝不断寻找策略。因为它不能将所有藩镇一视同仁,而应该有先后缓急的顺序,比如淮西镇特殊的地理位置,以至于它对帝国的生命线——几条主要运路都有极大威胁,所以这种对国家造成威胁比较大的藩镇就必须铲除,但是有的藩镇就可以缓一缓,先不处理。
大家都知道,很多王朝的执政理念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摸索的,德宗皇帝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觉得两河的藩镇都要收拾,手下的大臣也没有反对的。我很喜欢讨论这样一个君主,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唐帝国的繁华,到他差不多成年的时候就遭遇了安史之乱。我为什么说这个皇帝我比较喜欢?在唐代后期,德宗对他的父亲、妻子、小孩都比较好。他在奉天兴元之难的逃难途中为爱女唐安公主的去世造砖塔,当时的谋士陆贽等都劝谏说不要在这种军费尚且不够的情形下花钱兴土木,但是德宗坚持要造,而且唐安公主也一直被认为是非常孝顺的。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都非常疼爱。其中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在读《太平广记》时看到的,有一次德宗把孙子宪宗抱在怀里问他:“汝谁子,坐吾怀?”宪宗说:“吾,第三天子。”这个故事就和我们现在平常人家爷爷逗孙子一样,但在唐朝这样一个前前后后帝位继承总伴随着血腥政变、家庭悲剧的时代,你会觉得真是少有的有人情味啊。因此我想说的是德宗30岁左右顺利即位,是一个心智比较成熟、健康的人,他看问题并不是很极端,也不会一意孤行,但是他毕竟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见证了唐王朝的盛衰,而他的祖父、父亲帮他平定了很多事情。德宗有这样一个愿望,也觉得看到了恢复江山的可能,事实上他和杨炎最初在对付吐蕃与处理京西北、京西南藩镇问题时是很成功的,在进行讨伐两河藩镇的过程中,他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投入战争,甚至把宫殿的禁卫军都派出去作战,这是需要有很大的魄力的。当然在德宗遭到一连串打击之后,他的想法就变得逐渐现实,包括他晚年猜忌心加重,把权力抓得很紧,又喜欢敛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因为他敛了这些财,为宪宗后来的平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样我们看到,唐廷对藩镇的策略是在不断改变的,同样藩镇对朝廷的策略也会因此变化,双方都是一种不断博弈的心理。但是无论如何,对之后的宪宗来说,河南的问题已经基本可以解决了,而且策略、步骤都是很完善的。至此,这条脉络基本理清楚了。
不过呢,河南的问题写至此,并没有把我所有的困惑解决。平卢军的势力被打击肢解了,河南的危机好像结束了,那么后来呢?河南藩镇看似此后总体比较顺服,但它内部不稳定的情况还是有的,有时还很明显,而在黄巢起义后,河南各诸侯是整体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了,这又说明了什么?于是我就要研究在平卢系之后的河南藩镇变化出现在哪些地方。有些学者认为宪宗朝平定了河南藩镇,好像它的“中兴”就完成了,但我发现唐朝平定各个藩镇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宪宗的时代,宣武就已经呈现出地方军人非常跋扈、不断干预节度使人选的情况了,但这在早期的平卢系藩镇中是没有的,在早于安史之乱的藩镇中更不可能有。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这个转变可能是因为藩镇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地方军人已然崛起了。
关中藩镇的布局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按照前面说的思路,我同样首先需要搞清楚藩镇格局的变化。说到关中的藩镇我们首先都会想到朔方军,至少我写关中之前对其他藩镇也不太熟悉,比如凤翔、邠宁、鄜坊、泾原等,它们的名气也不大,在唐后期的表现似乎也不那么活跃。后来我看到有些学者指出,关中八镇的布局是为了对付关中附近的异族,比如吐蕃。这些研究对各个藩镇的目的、作用、职责解释得非常清楚,但他们的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把唐后期的关中八镇看作一个整体,把唐廷对八镇的设立看作是一个精心规划后的产物。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唐朝统治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是他想要怎么设计就可以怎么样。在唐和党项、吐蕃等的交锋中,有时候是“被布局”的情况,“被布局”就是说唐朝只能应战,因此关中八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哪儿有异族威胁就在哪里设藩镇,敌人打到哪藩镇就设到哪。另外呢,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中的藩镇都是沿着几条河谷设置的,因为这几条河谷就是关中通向渭河平原的交通线,同样也是异族进攻长安的方向。
当然,上述这些问题只是把最基本的框架理清楚了,我们对关中的分析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主导这些藩镇的力量上去。中晚唐时期关中的藩镇力量是很弱的,但我们知道以前它不但不弱,而且很强,因为它是抵抗安史之乱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其核心就是朔方军。于是我们就自然要关注中晚唐朔方军的力量有怎样的变化。
我把朔方军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以此来呈现唐廷是如何把它的股肱之臣的势力一步步压缩,比如通过撤换官员、分割权力等。但我们知道,要更换一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德宗和他的宰相杨炎是精心计划好的,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在这个布局中,唐朝还要考虑吐蕃的问题,不是把军事首脑都撤掉就解决了,还要考虑和吐蕃应战的情况。在中晚唐历史上,朔方军的统帅郭子仪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不断地被起用,又不断地被打压,但是朝廷遇到棘手的问题还是要找他,郭子仪在这方面也还是很有话语权的。另外,在关中由朔方军主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藩镇,比如原西部军团的主要力量——河西、陇右的军队怎么办等问题,也要为这股军事势力安置出路。
在研究中我发现,除了以上这两股势力主导关中外,其实还有第三股势力介入了关中,那就是幽州军。这是我在写这一章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是在研究奉天之难时发现,除了泾原兵变、李怀光叛乱等我们已经熟知的事件外,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弄清楚,那段时间我花了很大精力来写这部分,我不断在《奉天录》、《资治通鉴》中找这些细节来研究幽州军怎么会从东北跑到关中,在变乱中它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当我弄清楚这些事情后,我进一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发现唐朝对关中的这些藩镇都是很打压的,这就和河南的线索一样了,在河南是打压平卢系藩镇,在关中就是打压这些军团,虽然他们曾经是功臣,但是他们力量太大,对统治造成威胁,所以该打压的时候还是得打压。
唐朝在打压关中藩镇的同时,也需要培养一支可以信赖的嫡系力量,神策军就是这样出来的。我写神策军的时候,一开始有点难受写不出,一方面它当然是关中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势力,写关中藩镇的问题绕不开神策军。但一开始我觉得作为禁军的神策军,它的空间结构怎么体现出来呢?空间结构的变化毕竟是我这本书的明线啊。而且神策军的资料,至少传世资料,已经由日野开三郎和张国刚两位先生搜集得差不多了,新出墓志当然还能补一些,但毕竟有限,我还能有多少写作的空间呢?所以我刚开始构思神策军这一节的时候感觉有点苦恼,于是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百无聊赖地在地图上拿《通鉴》里的那条元载和鱼朝恩争夺神策军镇的史料来标记,这是有关中晚唐神策军镇的一条重要资料,之前的学者都用过,这条史料里出现了将近10个神策军镇的名字。真是不画不知道,一画突然问题就出来了,我突然发现神策军的几个据点都集中在西面的凤翔一镇里,而且分成三排排列,我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了。其实也很明显,这三条平行线就是三条交通路线,这些神策军镇的分布全部在交通枢纽上。
明了这一点还不是最令人惊喜的,更重要的是,前辈学者虽然搜集整理了传世文献中不少神策军镇据点的资料,但他们没意识到,这些资料的绝大多数来源于三条主要史料中,一条就是刚才讲的《通鉴》有关代宗朝元、鱼争夺神策军镇的资料;一条则是《通鉴》宪宗初年胡三省注中的一条资料;还有一条也是《通鉴》胡注的资料,但是正文是穆宗初年的。尤其是后两条资料,都是较为系统的神策军镇资料,且军镇名称不同,一旦把据点标示在地图上,反映的形势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真是相当激动啊,我当时就已经隐约感到了,这三条资料的时间并不一样,应该是反映神策军镇三个不同时期的,又因为它们是系统的,所以完全能反映空间变化的问题,而这个空间变化是能反映唐朝关中军事格局和军事措施变化的。神策军从最初为了对付吐蕃而集中在凤翔,到后来逐渐遍布关中地区,晚唐时期又收缩到近畿地区,这就说明异族威胁和唐廷应对变化的一个情况。当然在文章中我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做考证和搜集出土碑志的工作,但是这节的写作更告诉我,同样的一批材料,而且是这类看似只能做定点考证、且已经被前人反复研究过的琐碎材料,换个视角,能看出另一个更立体的面向。从这点上来说,有分歧的史料并不是可怕的,事实上,它常常是上天赐给你最佳的进行分析的宝贝,一定要好好利用。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这章中的“京东”部分,你为什么写不出这种比较立体的变化呢,事实上这部分确实是整本书中写得最一般的。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如果任何地区、任何问题历史都能够留给我们这么丰富、有趣的材料,那简直就是奇迹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也要允许论着的写作是有高潮有低谷,有可以写得更精彩一点的部分,也要允许有写得相对平庸一点的部分,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另外退一步找个安慰自己的借口,从写作的技巧上来说,在保证篇章结构大体均衡的前提下,有详有略,论述风格稍许有些差异也未尝不是锻炼自己或吸引读者的一个手段,所以“京东”部分和“附录”中的墓志伪作事件风格稍微不同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河北:安禄山的老巢
接下来就是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这部分了。我在写作河北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大家一直认为河北作为安史叛乱的爆发地,它肯定是很牢固地掌握在叛军手中的,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旦你真的一步步地去分析安史叛乱的整个过程,你突然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它不仅没有完全控制在安禄山的手中,而且在河北,不同地区对安禄山叛乱的反应也完全不同,这导致了河北地区始终呈现出一个不断反覆于支持叛军还是反对叛军的过程中,而且区域变化非常清晰。比如南部的滨海七郡始终不太支持安禄山,不断地给它制造麻烦,但安禄山对幽州一带的控制就一直比较牢固,那一块地方就不反覆。另外,中部的常山郡是一个很重要的郡,它治下的井陉关是山西进入河北的太行山中的孔道,常山的得失与否经常是河北反覆的锁钥。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同样是安禄山的辖区,为什么南部会时不时地反抗安禄山,但北部就不会?而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到唐前期的历史中去寻找。我发现,在安禄山叛乱之前,河北的军镇结构就已经有了变化了,管理异族的羁縻府州基本上都集中在幽州一带,培养骑兵部队的军镇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北京以北地区,但南部平原地带的军队则主要以团结兵为主力,尽管这些团结兵的战斗力也很强,但毕竟是一种类似民兵的组织,和正规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面对北方强大的铁骑时,南部的团结兵很难抵挡。这样河北军团的情况就清晰了。而且河北军团的情况并不全是安禄山一手制造的,在唐前期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情形了,因为河北北部必须要对付北边的契丹、奚等,而安禄山只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了这种既定的军事格局,并将之充分施展运用到他的叛乱军队中。即他带领北方的铁骑扫荡了帝国的河南、渭河平原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将领、军队都是安禄山手下战斗力最强的,而团结兵则被留在了河北的地方上。但安禄山没想到,在他的大军走后,类似于团结兵的河北地方民兵就会不断地反水,所以安禄山才要不断派史思明这样的人和军队去稳定河北这一后方。
有人认为安禄山研究清楚了,就能把安史之乱搞清楚了,但不是这样的,安禄山死了还有他的儿子,之后还有史思明及其子嗣。我在写作的开始阶段觉得安禄山死后的政治问题是不是可以简单一点一起写掉算了,但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安禄山死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这些问题非常有趣又很重要。比如安禄山死后,他的儿子安庆绪的号召力变得不太一样,手下的大将逐渐离心离德,这对自立的安禄山集团来说是出现了一个危机。取而代之的史思明以及那些和他平起平坐的、称王的高级将领都不傻,那么史思明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一些安禄山的亲信必须除掉,但是有些人却不能动,比如安禄山手下的那些高级将领。史思明也有手腕,用高官和虚位解除安禄山时代一些异族高级将领的军权,并且开始培植自己的牙将亲信,换一批可靠的自己人。比如现在我们从成德的《李宝臣纪功碑》中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一些不是安禄山时期的将领,可能是史思明时期涌现出来的。另外,蓟门内乱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不光是我们印象中的很多河北胡人在此次事件中被杀掉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未来河朔三镇的走向。
写完河北的安史之乱,当然接下去就要面对著名的“河朔三镇”了。于是又要对学界的常识性认识产生质疑了,既然河北在安史之乱前后就已经有差异了,那么其后身河朔三镇难道就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就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可以对他们一视同仁了吗?如果有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叛与不叛、跋扈与不跋扈的问题吗?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在于三镇的内部结构。譬如成德镇,因为幽州军乱,史思明时期的将领都把人马带到了李宝臣的成德镇,使之成为一个继承了安史旧部最好的衣钵、拥有大批精兵强将的藩镇。李宝臣就是利用了这个过去的权力结构,依靠这些骑兵力量把初期的成德打造成河朔三镇中实力最强的。自然,他也没有必要再去招募地方军队,因为手下已经有了这么强劲的正规军了。
但田承嗣就不一样,他的魏博在河北南部,尽管他也有野心,但是实力不足,他的身份也吸引不了更多的安史高级将领,那就只好白手起家,把地方上的军人收编到自己麾下,魏博的地方势力就是这样抬头的,著名的魏博牙军也就是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但一开始,他手下也有一些将领,也吸收了一些粟特将领,但随着地方势力逐渐崛起,这些原有的将校势力衰弱了,牙兵崛起的后果可能是最初建立他们的田承嗣完全没有料到的,魏博的权力结构也就这样逐渐被地方低级军校、军人把持了。
幽州可能走得又是另外一条路,它的主要将领不是牙将,因为幽州有一条很长的北部边境线,所以需要把最优秀的将领配置在边境,它的经济特点也与南方的两镇不太一样,所以幽州最强的势力是北部的军镇。这就是河朔三镇最重要的区别,而这种差别也会影响到它们和朝廷之间的关系。
前面我们一直在谈河北内部的问题,当然,河朔三镇和朝廷的关系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我发现,唐朝对河北的态度与它对河南等地的态度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只是与朝廷日益重视河南等地不同,它对收复河北却越来越不上心了,只要河北三镇不与中央作对就行,也没有把河北地区重新纳入掌控的要求。有些政治家比如李德裕,话就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河朔藩镇还承认中央政府,朝廷也不会干预藩镇的地方事务,这就是在现实政治环境下表现出来的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其实李德裕主政时还对河北周围河东藩镇的人选作了很好的安排,我在书的注释中也提到过。他辅佐几任并不杰出的皇帝,但本人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以至于我当时写文章的时候,在河北与朝廷关系这个问题上花了比较长的时间,那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渺小,因为我一个每天宅在书房挤论文、尚未踏足社会的小姑娘,却要洞悉一个唐朝最一流政治家的想法,常常觉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部分写作有时候我会停顿个半天、一天,因为觉得李德裕太了不起,面对他我有时真不知道还能讲些什么,但他的最后命运却是可悲的。我们做政治史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要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都是古代的那些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考虑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他们早已考虑到了,所以千万不要低估古人的政治智慧,更不要随意褒贬,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尽自己的努力站在他们的立场,试图了解他们的所行所为,仅此而已。
永王之乱和军将
最后一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部分“永王之乱”,因为第四章其他部分在硕士论文时基本都写好了。我原先只是想把永王之乱稍微理一下,没想到结果写成了整本书里最长的一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用了十个小标题来规划这一节。写完之后突然觉得,希望有哪个编剧,最好是戏曲的编剧,能看到我这个东西写个剧本吧,就写永王之乱,你可以从中读出很多内容和情感。这个事件就像十幕剧一样,我最后一个小标题就叫“谢幕”,写完的时候我确实是很感慨,觉得满眼悲凉,那时还是春节前后。你可以看到安史之乱时期的中枢斗争是如何影响了很多士人、军人,甚至普通人的人生轨迹,个人的命运在政治风暴的裹挟下是如何微不足道与不堪一击的。
写作过程当然也不轻松,因为永王之乱的史料不断被篡改,面对被篡改的史料,你如何把史料中被篡改的部分和真实的部分、对研究有用的部分和后人想象建构的部分区分清楚,尤其是还要面对之前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学者,你还要把他们理解的对的或错的部分吸收消化,头绪确实比较烦杂。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心理史,永王之乱中有些诏书可能是伪造的,但这个伪造出于什么动机现在还只能推论,我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确定某些推论是正确的,只能说按照逻辑推理思考它可能是伪造的。不过这一节的写作也是很过瘾的,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原因外,新出土文献、笔记小说、诗文的资料你都可以运用,都可以想办法把它们串在一起。
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对江南地区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被一些北来将领所吸引。当我在读本科写韩滉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柏良器之类的军人。但他们不是那种蠢猛的武夫,你看李翱撰写的《柏良器神道碑》和其子柏元封的墓志,说柏良器出身儒学世家,父亲曾是射策甲科的获嘉县令,在安禄山攻陷东都时,持印不去因而被害。于是柏良器遂学剑从戎,将复仇以快冤叫。后来他年纪轻轻就被府主李光弼派往江东平定地方动乱。安史之乱结束不久朝廷派了李栖筠,也就是李吉甫的父亲、李德裕的祖父来担任浙西观察使经营乱后的江南。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两《唐书》也不知道碑志里有一处记载说,李栖筠看到柏良器后问他的生平事迹,后者回答说身经大小几十仗,然后李栖筠立即很郑重地向他致敬,说了句好像是“有公如此,得公甚深”之类的话。我当时读到这句话非常感动的,因为我推算了一下,柏良器当时的年纪在二十四五岁左右,比当时写论文的我也就大一两岁吧,而李栖筠的年纪推断下来估计和我父亲差不多大。一个相当于父辈的人在初次见面时能够对一个手下的年轻人说这样的话,放在今天也不多见吧,但安史之乱的时代却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李栖筠和柏良器的作为,怎么能叫人不感慨与动容中唐人的精神,而有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一批人,唐帝国又怎么可能在安史之乱后就灭亡呢?你当然也可以说这些文本的写作可能有溢美之词,当然会有的,但这种遣词造句被用于形容当时很多的将领,比如永王之乱时的季广琛、刘展之乱时的李藏用、韩滉时代的王栖曜、李锜叛乱时期的张子良,无不如此,那就是一个时代风尚的问题了。而且这些将领和当时知名的文人关系极好,比如韩愈、李观辈都曾游于后来成为神策军统帅的柏良器幕下。
我想很多人都会喜欢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琅玡榜》里的梅长苏,我也很喜欢,那是一个虚构的由武转文、亦文亦武的人物。但你看看中唐的季广琛、柏良器这些到江南来的将领,他们可是活生生地由文转武、或者说文武兼备的人。而且真实地生活在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动乱年代是很能见一个人真正的风骨的。这也正是我非常喜欢中唐这个时代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宪宗朝之后,这些将领的身影就逐渐不见了,随着宪宗平定李锜之乱,江南的藩镇面貌也发生变化了。文士取代了韩滉这样的贵族节帅、“土豪”取代了曾经的这些北来将领出现在未来的江东舞台上了。
重构了什么?
到这里,我用四章内容把各个地区的“危机与重构”问题都作了梳理,但对一篇博士论文来说,还必须对主题做个明确的交代,于是我就在代结语中把“危机与重构”作了总结——安史之乱究竟带来了哪些危机?重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的?
最大的危机当然是安禄山叛乱本身。它反映的问题就是杜佑所说的,在唐代边境线上有两个大的军团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晚唐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没有成就,它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它借助安史之乱这个契机,包括之后一连串的战争和政治策略,把两个大军团的力量不断打散,到了唐宪宗《元和郡县图》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藩镇能有力量与朝廷叫板了,这样一个帝国在我看来当然是成功的。面对这样巨大的挑战,在化解的时候如此成功。
当然除了空间结构的重构外,唐帝国化解危机时的“洗牌”做得也非常干净,那些实力强大、骄横跋扈的旧藩镇势力最后都被除掉了。不过政治史研究有一条定律,那就是政治权力是不会出现真空的,当这些老牌的势力退出的时候,必然会有新的力量来填充它。河南有非常强势的地方军人,包括后来五代的那些创业者基本都是地方军人出身。关中虽然资料有限,但隐约可以看到京师神策军的身份主要变成了长安的富家子弟。河北藩镇因为情况各不一样不太明显,但魏博很显然也是地方军人非常强大。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讲的江南,因为这里代表了未来宋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土豪”,他们往往是一些大土地所有者或商人,但也有一定的武力基础,比单纯的职业军人对未来发展的走向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个群体也登场了。这些就导致了除藩镇空间以外的另一种“重构”,也就是社会阶层的重构。
而在我看来,社会阶层的重构应该是唐宋转型中最至关重要的一点。唐宋转型是从2005、2006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比较热的话题,我很庆幸自己是在这股热潮掀起之前开始读日本学者关于唐宋转型的书籍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日本学者会在战后把他们的关注点都放在这个大问题上呢?你去看日本学者不管从哪个层面谈唐宋转型,都会谈到身份的问题,而涉及身份最重要的法制、经济研究又一直是日本学者的强项,包括和我的研究最相关的军制研究也是如此,都集中于一个问题,就是身份变化,他们不断讨论国家的人身控制等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在战后面临着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同、落差、重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后来我在和一个老师聊天时谈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代变了、转型了?你可能会觉得工资、收入、生活水平变了,这当然是有变化了,但可能我觉得比如对在座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曾经大学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群体,走在路上是可以抬头挺胸、80年代或90年代初哪家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很光荣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家很多时候会感到迷茫,感到大学生满街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之类更是不好找。而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转型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你身份变化产生了落差。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社会重构的问题,你会感慨时代变了。
当然我在文章里面还谈到另外一个重构,也就是我发现唐帝国在对各个区域的认识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现在会把河北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把重心放在江淮,第二个放在关中或者河南,它对每一个区域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出现。唐朝关心江淮是因为江淮成为经济命脉,关心关中是因为首都在这里,是文化中心,关心河南是因为关系运路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河北对它来说就意义不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唐代人对于它的地区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排序了,而这又可以和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对上话了。仇老师以前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讲唐代的关中与山东关系的。为什么前期可以这样写?包括汉代你也可以写关中和关东,这个情况是因为前期这两个地区都比较独立,唐代通过关中一地可以满足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对外部的控制相对来说就弱,关东也很独立,两者就会出现对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在逐渐变得会以明确的地区分工的形式,各个地区扮演不同角色的面貌出现了,这时唐帝国就不能只靠关中一个区域来维持了。如果它能维持的话,为什么武则天要不断到洛阳去就食呢?因为经济方面关中已经维持不了了。再回过来看安禄山,他当然会坐大,因为军事压力在北边,当然要发展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是一定要给安禄山多大的权力,而是不给这些权力就不能让他们有效抵抗异族的入侵,而且必须实行权力集中,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再往大的层面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了,中央不能仅仅是依靠一个本位的地方来维持了,必须要不同区域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彼此密切配合才能维持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是这个趋势的产物。但是这个转型确实就是发生在藩镇时代的,虽然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在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实际上地域之间的融合却越来越紧密了。而到了宋代,宋人比唐人更觉得边地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那时人的想法都已经很现实了,所以会有太祖玉斧划界一说,而且是美谈。这就是另外一个重构的过程。
过去我们对盛唐谈的太多,一提到唐朝那就是盛唐,总让人想到繁荣昌盛的景象,现在很多宣传中国文化的文艺演出也总有大唐盛世的篇章。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中晚唐的政治魅力,避免产生那种忽视中晚唐的心态,其实一个看似藩镇割据的中晚唐给后世提供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表面的分裂遮掩不了它的政治光芒和时代价值。中唐在危机下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更考验政治家的智慧的,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考验着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所以我能够碰到这样一个题目,确实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谢谢大家。
仇鹿鸣:似乎学者都希望自己好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我印象中上一个在讲座中提到类似话题的是黄一农。(众笑)
回到正题上,其实藩镇是一个非常旧的题目,或者对于一个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来说,难免要面对的挑战是,由于中古史领域中相对材料少而研究者众多,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会遇到找题目的问题。比如藩镇,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晚唐研究的热点,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藩镇有大量个案研究,几乎每个藩镇都已经有相关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对题目的焦虑。但是在个案研究的浪潮下,很多问题都被遮蔽了,就像李碧妍刚刚讲的,每个个案都是差不多的面貌。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想法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预设,觉得中央权力衰弱的时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所以在任何一个对地方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不是关心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关心它和唐王朝的关系。于是任何一个藩镇都会有恭顺期、跋扈期、叛乱期,这些对应的研究对象就是藩镇节帅,或者其一些手下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研究下你会觉得每个藩镇的脸都长得差不多,似乎每一个藩镇都有从恭顺变得跋扈,然后被唐廷镇压或进一步自立等等类似的戏码,尽管每个个案都不一样,但事实上观察问题背后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研究时需要反省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本书很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完整处理了一个时代的断面。对于一个研究的初学者来说,相对容易入手的是个案研究,因为个案容易把握,材料也比较集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所谓“截断众流”,在一个横剖面对一个时代进行观察,但这就要面对非常庞大的先行研究,还有对于如何来理解这一时代及其意义这样大的设问。个案当然可以做出很精致、精彩的研究,但是真正重要甚至了不起的研究恐怕还是需要有一个“截断众流”的取向,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且在一个横向的剖面上,它可以展示出在历史转折的时代,面对这个危机,整个藩镇的体系是如何建立、分合和调整,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在历史剧烈变动时,所缠绕着复杂政治和人事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纠葛,把握时代的脉搏。当然这从研究过程本身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可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和最具有魅力的题目。
就中古史的研究来说,既有容易的方面也有不容易的方面。不容易就是既往的研究积累非常丰厚,现代学者往往面临着似乎没有题目做的困境,但是反过来我们的前辈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刚刚说藩镇是一个旧题目,包括李碧妍提到的日野开三郎等日本学者及大陆、台湾很多学者都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过去的学术脉络下,对藩镇的制度和构造作了非常精细的研究。我个人感觉过去对藩镇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及制度面向的,对于藩镇的政治体制、军事体系、财政结构等方面研究得相当透彻,但相对来说对于藩镇动态变化的过程把握相对欠缺。但中古史研究的好处就是,由于之前很多优秀的学者做了很多基础性及相关性的研究,一旦你寻找到新思路,能够打开新的方向时,你觉得过去很难跨越的前辈学者的高峰,现在反而变成了你研究的重要支撑,你能很快找到各种各样的基础性、考证性的研究,为你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的方便,真正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使得之前讲的“截断众流”成为可能。
第三点我想说,对于一般历史学出身的同学可能注意不够,是李碧妍对空间这一分析工具的利用。其实历史学两个最主要对话的对象,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李碧妍读的是历史地理学,对于空间具有敏感度,某种意义上这本书能被归入周振鹤老师提倡的政治地理研究的脉络中。周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行政区划是按照两个基准来设计的,一是山川形便,就是按照山和水这些天然的界限来设立行政区划,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犬牙交错,故意把天然的界限打破,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从汉代到现在中国县一级的规模基本上是不变的,数量也较为稳定,但越是高层的政区变化越大,因为高层政区的设置更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藩镇恰恰是在应对国家的危机时设立的一种准高层政区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藩镇的兴废、分合、调整、合并背后都有或隐或显政治原因的推动,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和空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另外,尽管我们一直都把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过程的理解往往是单线式的,把安禄山等人和唐王朝作为对立的双方,把战争看作双方围绕长安、洛阳地区的拉锯,我们基于这些“典型”或者“重要”事件(比如之前碧妍提到过的张巡)所构造出看上去清晰而明确的历史画面,但实际上这个画面应该是复杂的。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古人想得比较简单,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喜欢给政治人物贴上标签,并把这个标签就作为贯穿这个人物一生的主要线索,比如某党、某派。但事实上,人物应该也是复杂的,你不能把一个人视作标签式的人物,他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在政治立场背后他会有实际的政治利益与交换,这些会影响或决定他政治立场和态度。
就像我开始时候说的,历史需要被充分的展开,从这个程度上说,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细节的呈现。如果你要做解释的话,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科学在解释能力方面要远远超过历史学,这时我觉得呈现出复杂性某种意义上是史学家的责任。
第四点可以讲一讲对于中晚唐的观察。我感觉唐代的前期和后期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变化,唐代前期是一个比较均质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中央对每个地方的控制力是均等的。所以对唐前期的观察,我们依据《唐六典》、《通典》等对相关制度的记载,容易得出唐代前期是整齐有序的印象。但是唐代后期,其实并非没有材料,而是材料零碎和散乱的,从我最近几年的工作来说,认为唐代前期和后期政治的区别在于,唐代前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制度性的规约来展开运作,但唐代中后期更多是依赖于政治的惯例或政治的默契,这些并不行诸文字,这时需要研究者通过对于政治行为的分析来勾勒出线索,发现这些默契与惯例是如何起作用的,难度当然更大一些。
比如书里相当篇幅讲到唐德宗,如果我们不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从生活在历史情境中的人物来说,德宗安史乱后首选自然是要努力恢复盛唐的格局,再造盛世,所以在代宗、德宗、宪宗时期中央和藩镇会有这样激烈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是对峙的双方都认识到了,互相力量的边界所在,所有的政治惯例、政治默契都是在不断的博弈中形成的,最后这就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运作。而这种默契和以前那种载于史册的制度来比较的话,它有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面向,只有在政治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我想从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我们应该去试着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在最近二十年,不仅是中古史,整个中国史都迎来新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的研究衰落,当然这也受到西方包括港台一些研究风气的影响。确实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一般人的历史,按照年鉴学派的说法,一般人的历史是沉默而恒定的海洋,而政治事件只是海面上的几朵浪花而已。这话当然很有道理,而且我对于新史学也非常有兴趣,但是回到中古史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在过去的研究中,那些重大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讲,这些结论更多只是一个性质的判断,但对于结论背后的支撑它的史实,包括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其实是缺乏研究的。而且我们现在提供的结论往往带有不小假说的性质,但现代有些研究干脆是站在这些结论上展开的,但对于这些假说本身是不是足够可靠,在我看来都是需要加以反思和回应的。在我的观念中,学问没有新旧的,只有好坏,套用胡适的话,我是一个“好研究主义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在充分地掌握史料和前人对话的基础上,揭示出不同的历史层面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从目前而言,我觉得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应该到了需要重新加以检讨,至少对于重要的假说都需要有所反省。
所以我觉得李碧妍这本书填补了一些空白,对于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到底能不能提供一本比较好的专着,构成将来进一步讨论难以绕过的基石,我觉得她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份答卷。
《危机与重构》读后感(十):唐帝国在时间与空间下的自救
新年读完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推荐给朋友一起阅读的第一本书。选择这本书的原因,主要是被题目和介绍内容所吸引——对唐代中晚期,藩镇势力的考察和研究。
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性读物,这本书翻开之后就被震撼。这本书李碧妍博士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而来的。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庞大的古文,旁征博引,每一个观点和结论的抛出,都是小心翼翼,经过梳理和考证的。
本书的结构也非常有意思,正文一共四章,按照唐帝国四个不同的地域一个个讲述。但是每一章讲述的方式都不同,力求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下,讲清楚中晚唐如果面对危机与重构自身。
第一章——河南地区。读起来最吃力的一章,能够看出来作者的野心勃勃,想要从时间的角度去梳理,安史之乱发生时,唐廷在河南地区面临的危机的解决。和平叛后,河南地区对新兴藩镇的政治的重构。这一章也奠定了全书的基调,点出了唐帝国所面临的四个危机中的三个,安史之乱、唐廷内斗、新兴藩镇。其中对于平卢系的梳理和分析,非常的精彩。
第二章——关中地区。作为唐廷的政治中心之所在,本章作者又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去梳理“京西北八镇”,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势力的变化,以及这种空间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从而引出了唐帝国所面领的第四个危机:异族的威胁。
第三章——河北地区。安史之乱的发起点,作者这里又换了一种思路,转而分析异族蕃将为主的“河朔三镇”的“藩镇性格”。也就是藩镇的构成、演变和更替。唐廷对于边军藩镇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度的变化。《刺客聂隐娘》的故事就是在其中的“魏博”。
第四章——江淮地区。比较遗憾的一章,作者想从永王东巡和刘展之乱去梳理唐廷的内部斗争,但是感觉没有前三章的节奏感好,而对韩滉和镇海军的梳理还算不错,加上最后的李琦叛乱,整个章节稍显凌乱,没有前三章舒服。
后面还单独讲述了李怀让之死,讲的非常有趣,不过感觉像是单独的一篇文章附在书里一起的,不太成体系。
总之,这本书确实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书。作者用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梳理了中晚唐时期,不同时间和空间下藩镇的演变。藩镇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让唐帝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更是很远的影响到了中国后续的历史。
最后附一张我自己整理的全书脑图:
《危机与重构》
请用微信扫添加公众号